
《中产阶级看月亮》是萧耳的一部长篇小说,曾发表在《钟山》上。小说主人公宋青瓦和冯春航,是一对浅交集、有好感的男女,在人生的时间轴上,他们擦肩而过,另娶另嫁;多年以后,青瓦在平淡婚姻中感到厌烦无聊,从记忆里打捞往昔,终于想方设法与春航重建联系,并顺理成章成为情人……
这是一段心灵之爱的旅程,主人公青瓦和春航沉浸在精神层面的契合中,然而,往昔的激情与默契,终究会归于平淡,爱情也终究归于幻灭……
小说里面的人物关系处理得非常美,非常干净。与生活贴得很近,很绵密、很充沛。很多城市文学、中产阶级文学都只是停留在城市生活的表层,但《中产阶级看月亮》则通过这些描写,写出了都市生活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情感世界。
编辑推荐
李洱、梁鸿、艾伟、路内、鲁敏、贾梦玮 倾情推荐。
萧耳勾出了中产阶级男女的魂;
深陷婚姻围城中的渴望与突围;
20年后的你,还会仰头看月亮吗?
中产阶级看月亮就是个冷笑话。
精彩书摘
昔日经行人去尽,寒云夜夜自飞还。
——僧 皎然
1
有一天,青瓦和五岁的女儿未央一直在翻米罗的画册,未央指着一幅画,高兴地说,妈妈,我要爬这个梯子,爬到月亮上去。米罗的画的确很有趣,画中有长长的梯子和大大的月亮,可是青瓦却觉得,那个特别想借着梯子爬到月亮上去的人,是春航。
属于春航和青瓦的典型夜是怎样的呢?比如这个夏夜,春航在沈阳的宾馆房间,有点醉了。他在那顿饭局上喝了半斤白酒,结束了所有应酬才回到宾馆。春航给青瓦打电话,以平静的声音说了很多话。春航讲,我们是熟悉的陌生人。春航就是爱这么闪烁其词,娘胎里带出来的。青瓦记得一部法国电影叫《亲密的陌生人》。海报上,一男一女两张脸紧绷绷的,有点疑虑,有点惊悚。
第二天春航醒来,一天都在谈判桌前跟人争来争去,就到了晚上。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春航在宾馆的床上,青瓦在自己的床上。春航讲,昨天我是不是唠唠叨叨的?青瓦笑而不言,春航的辞令都是一套一套的。春航讲,我完全不记得自己胡说些什么了。青瓦却记得春航讲过的大多数话。另一些话,因有时手机信号不好,被蒸发在稀薄的夜空中了。
昨夜春航讲过的话,包括熟悉的陌生人,一张餐桌,刷牙的动作,冬天被子冰凉的缎面,膝关节。春航夜里想起松尾芭蕉的俳句:“芒鞋斗笠,春夏秋冬又一年。”有少许流水落花之叹。意象是分散的:一个朋友的意外死亡。一个十四岁女孩和二十岁男孩组成的水粉画。秋天的黄叶,冷落的池塘,夕阳下的紫藤花。女孩不是青瓦,是春航太太慧梅。春航苦恼道,我要完成那幅画,可是,我现在笔头涩。青瓦不知怎么接口,春航讲,好像记得就是我在那里不停地说啊说,是不是有点烦?青瓦道,你尽管说好了,我爱听的。春航在画的画是送给慧梅的,今年是他们结婚十周年。
春航第二天要赶去京城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逝者是位少数可以称得上谦谦君子的人物,比春航小一岁,却要苍老许多。两人刚认识时,春航以为朋友比自己大很多岁。又是一个过劳死的典型。春航在电话里讲啊讲,好像自己也恍惚了,忽然就感伤起来,对青瓦讲,我说过的,你是我今生唯一的情人。青瓦抿抿嘴,安静听。春航讲,我说这个话,是非常认真、正式的。青瓦就说,我知道。
青瓦时常做梦。做梦真是件辛苦的事,梦境有时太复杂,醒来后会有些失落。找到春航后,青瓦心里踏实了,一连三个月都没做梦,又开始想回到有梦的日子,因为梦里的世界也是蛮有趣的。昨天晚上,青瓦读松尾芭蕉,读“绵绵春雨懒洋洋,故友不来不起床”,想自己就是那个故友不来不起床的懒人。这天入睡后,梦说来就来,还梦见了春航。
青瓦梦见春航在自己小辰光苏州老屋里,屋前一条小巷子。老屋里光线暗暗的,有张吃饭用的褪了色的红色八仙桌摆在屋里。春航坐在八仙桌边上,跟青瓦姆妈说话,像是唠叨家常的样子,态度谦和。青瓦安心地坐在桌子另一角,听人家讲。春航穿咖啡色夹克,季节应该是深秋。后来老屋子又多了一个人,来向青瓦求婚的洪镕进来了,也坐下说话。洪镕在八仙桌的另一边,穿着蓝或灰的西装,不知道春航是谁。洪镕跟青瓦姆妈说苏州话。春航却听不懂。青瓦说,你、洪镕、我妈、我,围成了一张方桌,坐下来正好打麻将。
青瓦每次梦到春航,春航都在屋子里,屋子是暖色调的。以前青瓦梦见自己和男人去旅行。不同的男人,在船上、车上、海上、步行的旅途中,在一座寺庙的大雄宝殿前,那些旅途中的梦是浪漫的,身边的男人是青瓦的恋人,或者有那种无须多言的默契关系。有些男人的脸清楚,有些男人的脸模糊。美梦里,偶尔有肌肤之亲,青瓦在旅途中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打个盹,还有接吻。不知为何,那些梦里都没有春航。
青瓦是那样一种人,很容易被自己的梦影响。室内是一种凝固的温暖的调子,室外却是晃动的,流动的,人来人往。青瓦想,那些梦是否提供了一种暗示——自己与室外的男人们的关系是萍水相逢,只有春航,总是在屋子里出现。在梦里,屋子是否就代表一个人的心呢?有人说,总在梦里出现的人,醒来时就该去见他,生活就是那么简单。
春航在电话里回应,记得我跟你说过,你是我骨子里认定最适合在一起浪迹天涯的那个人。青瓦说,我想再做一个和你一起旅行的梦,就差这一个梦。在路上,我们两个。春航讲,这不仅仅是梦,会是现实。而且,不会只有一次。青瓦说,你不觉得我们已经过了浪迹天涯的年龄了?春航讲,我是说,如果。春航讲,记得我一个朋友说,女人就是男人的房子。男人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青瓦在电话里发出清脆的笑声,说,否则男人没有了房子,就成流浪汉了。又笑道,房子是阴性,公路是阳性,对吧?
春航讲,嗯,我知道,你总是喜欢把词语分成阳性和阴性。你说过的,万物都有阴阳,我记得呢。青瓦又笑,春航也笑道,那么说,我是被你软禁了,困在你的屋子里?青瓦说,软禁?我很想,但你是自由的。
青瓦从小到大做着迷路的梦。比如走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江南村庄,好像是小辰光待过的村子,下午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一个村子,影影绰绰地和一个个熟悉的人和地点相遇。天黑下来了,青瓦想这个村子离回家的路还有好一段呢,要回家了。可是走来走去,又返回到原地,总也走不出去。黄昏时,村子露出狰狞的面目。走在迷宫一样的乡间泥石路上,心里开始发慌,一路上问去杭州的路怎么走,然后就遇到了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要带去他们家的方向,有的男人还挡住去路,动手动脚。青瓦一次次地掉头就走,想立刻逃离危险地,很害怕会被男人关起来,失去自由,被戴上脚镣,当成女奴使用,沦为生育机器。后来就到了一条水流很急的小河边,只要顺着这条河一直到下游就可以回家,但是路很长,也许要走到天亮。青瓦看到河上有只小船,是可以顺着河漂流下去的,船夫说,五十块钱跑一趟。青瓦身上没有钱,就哀求船夫行行好,不停地哀求。天更黑了,船夫不肯。青瓦就哭了,一边哭一边沿着河岸走,想只要一直在河边走,应该可以走回家去。后来就一直惶恐不安地走啊走,直到醒过来。
春航讲,你做了个面临险境的噩梦。青瓦说,我是个路痴,对走迷宫很没信心。有一年和朋友去圆明园玩,那里有个迷宫,我一个人就走不出来,后来只好跟着别人走。心里对这些东西老是没有底。春航讲,心理学上说,迷宫代表某种不确定的东西。青瓦说,我从书上看到,本雅明有一次在巴黎“双偶咖啡馆”等人,就画了自己生活的一张草图,就像一个迷宫,在里面,某种重要的关系都标作“迷宫入口处”。本雅明还说,在城市里没有方向感,不是件有趣的事。我就警告自己,人生若没有方向感,也不是件有趣的事情。春航有点吃惊地问,你在读本雅明吗?春航大学时期听过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名字,觉得本雅明的东西颇为深奥。青瓦像是低语,我只是偶尔翻翻。只记得他说迟钝是抑郁症的一个特征,我的另一面的确不够阳光,像梅雨天气。春航温柔说道,我挺怕你这样的。你不开心的时候,要多想想我。
青瓦继续说她的梦。青瓦说,有一次梦中,我又走进了五岁那年差点让我淹死的太湖边的那片甘蔗林,在那里迷了路。慢慢地,两条腿向边上的池塘滑下去。为什么我的脚步不受控制,不听使唤?我想的是要离池塘远一些,结果却越走越近,好像鬼在向我招手。我的脚已滑到池塘边的过渡地带,很多的水草、泥浆掩盖了池塘的面目。春航讲,我把你拍醒就没事了。青瓦说,那次差点淹死的经历我现在已经记得很少了,但是几个关键地方还记得。那是个冬天,我记得那一天我是穿棉裤的,棉裤是我妈自己做的。我在苏州乡下上幼儿园,下午放学了,我跟在放学的队伍后边走,因为我妈工作忙不能来接我。渐渐地我因为开小差掉了队,离老师和同学们越来越远,后来我不知为什么钻进了甘蔗林。后来就一边哭一边走向一个池塘。可能我是滑下去的,滑下去后,我自己想爬上来。再后来的事情就模糊了。天越来越黑,走过那里的村民很少,不知是谁救我上岸的,又怎么把我送到我妈那里。我的棉裤全是湿的。那次我离死亡真近,一个人,看着天黑下来,一定又冷又怕。说完梦,青瓦又问春航,你迷路过吗?春航讲,当然。岂止迷路,还迷失过,如果你的人生是在雾霾中行走,你连自己家都摸不到。春航讲着讲着又闪烁其词了。
春航问青瓦,你说人的记忆是从几岁开始的?三岁还是五岁?青瓦说,我五岁的事情记得一些,三岁的事情,好像有些模糊的影子在飘,跟梦境混淆了。春航讲,我感觉人在时间里,一个人是他自己;在空间里,就变成另一个人。青瓦说,反正要说变成另一个人,我最想变成的人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想变成你,因为我最好奇的人就是你了。春航大笑,讲,变成我有什么好的,凡夫俗子,太普通了。青瓦也笑说,你是一条变色龙。春航反问道,变色龙?我复杂吗?青瓦说,你比我复杂。我现在就是一傻妞。春航讲,我傻根。
春航和青瓦,这时各自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都看到对方的嘴角咧开着,在电话里,听得到对方细微的呼吸声。
青瓦又感叹说,有人说,人越老,就越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春航讲,所以我们变得怀旧了。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我承认我是个胆小鬼。青瓦说,人人心里都有鬼,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有时候做了噩梦,吓醒了,人没有彻底清醒过来,迷迷糊糊又睡着了,结果还回到刚才的梦境里去,又接着做,像连续剧似的。有时候梦里跟什么人有肌肤之亲,像真的一样。春航讲,那还是做春梦好。人生如果是一场春梦,在锦被堆里颠鸾倒凤,那质量就太高了,或许人人求之不得。青瓦说,都想当旧社会的爷。就听到春航爽快的笑声。
青瓦俏皮道,肌肤之亲这种事,当时是有存在感,过后却是亦真亦幻、有等于无。我一个朋友这样说时,我很失落的。春航追问,是这样吗?比如做爱?青瓦轻声说,是的,所以你要经常抱紧我。春航讲,现在就抱紧你呀,宝贝。青瓦说,要经常亲我。春航讲,好。青瓦抒情道,我爱你的身体,还有,从身体里长出来的各种念头。春航就说,我爱你,只要是你。
话题像麻雀一样,从爱情跳到死亡。青瓦说,你离死亡最近的那次,害怕过吗?春航讲,当然怕死,只是后来一时半会儿又死不了,有些麻木了。这时青瓦林黛玉附体,感伤道,我老是莫名其妙的沮丧,害怕心里空了的感觉。春航了解,说,你是感性动物,我了解的。青瓦追着问,我了解你多,还是你了解我多?春航讲,没法比。青瓦又说,我羡慕你,有那么多姑娘都喜欢你。春航连忙说,你也一样,肯定有很多男人喜欢你。青瓦撒娇说,没有喜欢你的多,我敢肯定,因为你比我长得好看。春航就哄道,噢宝贝,男人好看有什么用!青瓦总算不追问下去了。
又说童年。青瓦问春航,你的童年,感觉好吗?春航讲,你知道的,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就没了。我这种野孩子,好几门功课大红灯笼高挂的,父亲没了我忽然一夜长大,家道中兴全靠我了。青瓦说,每次一想到你那么小就没了爹,我就心疼。
青瓦今天话多。不知不觉中,过了午夜12点。青瓦说,我关灯了,你关灯了吗?春航低声道,我躺在床上了。青瓦问,沈阳空气干燥吧?春航讲,还好,我多喝水。青瓦闭着眼睛,说,我在想童年的恐惧为什么一直忘不掉呢。大概是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8点钟不到的光景,苏州老屋里,只剩下我和我爸两个人。其他的人,爷爷奶奶叔叔堂兄们全去乡下做客了。我那天好像有点感冒发烧。我们的老房子就在一条河旁边。那时候这条河还很热闹,每天晚上能听到船来船往的声音,只要推开窗,就可以看到船在河上。20世纪70年代,样板戏正流行的时候,我家房间的墙上,贴着张《红灯记》的宣传画,上面是长辫子的李铁梅和她奶奶,她奶奶手里拎着一盏煤油灯,样子严肃。我爸下楼帮我找药去了,已经有一会儿了。从我们的房间要穿过一条走廊再下楼梯,我一个人在楼上,一抬头看到墙上的画,不知为什么,越看越害怕,好像那个很凶的老奶奶活了,正走下画来。然后我爸在楼下听到一声惨叫,赶紧飞跑上楼,就看到了我浑身发抖魂飞魄散的样子。总之,那张宣传画引起了我的恐惧。几年后,还在那老房子,有一次我偶然看到那张没有被扔掉的宣传画,还会紧张。奶奶的眼神里有一种让人害怕的东西,一种毁灭和不祥,所以小时候的我吓坏了。那天我们没有住在家里,躲去了亲戚家,直到爷爷奶奶他们全部回来后,我们才回自己家。我奶奶说,家里人少,房子阴气重,阿囡你撞到鬼了。总之,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很神秘,无法解读。我们搬家离开河边老屋前,整理旧东西,居然发现那幅画收在某个角落里,我还是不敢正眼看它,我知道是我妈干的,她在学校曾经演过李铁梅。后来我爸看到,跟我妈吵了一架,说为什么早不扔掉,让阿囡怕,这才把它扔掉了。
青瓦有些不确定春航是否还在听。春航讲,我在听。青瓦翻了个身。春航讲,我想起《红灯记》里的那老奶奶,其实并不可怕,只是表情苦大仇深。我小时候也是真正的革命年代,除了样板戏,还有一些其他的,后来看到《英雄虎胆》里的阿兰小姐,王晓棠演的,简直惊为天人了。青瓦说,我得向你坦白,我害怕很多东西,怕这怕那的,省得你以后笑话我。春航讲,我不笑话你。青瓦说,我怕很多声音。我上幼儿园前,在苏州乡下保姆家寄养,有一次保姆家的几个小男孩搞恶作剧,把我关进了猪棚,好长时间后才放我出来。那一次也许惊吓过度,从此以后我特别怕突然发出的声音,听到有些声音会忽然心悸。突然的雷声,汽车喇叭声,爆竹声,枪声,都怕。我到现在一到过年就紧张,最好就躲在家里,因为到处都在放鞭炮,连小孩在小区里放鞭炮我也不敢走过去,要捂着耳朵,肯定被当成笑话了。这个大人那么胆小。只有一次我是克服了枪声的,因为大学里要打靶。我趴到地上,豁出去了,居然打得不错,后来还参加过打靶比赛。但是过后,我又照常会害怕,那只是个特殊时期。春航讲,你不说,还真的看不出来,不像你的个性。青瓦说,我怕婚礼,因为总是要放爆竹。我忘了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春航笑道,那其实都是办给别人看的。我们自己呢,就像人家手上的提线木偶。
青瓦又讲,我很少和男人一起去电影院、剧院这类地方。一般关系绝对不去,宁愿跟陌生人一起跳舞。看电影、看戏的时候,两个人挨得很近,在黑暗中坐在一起,总觉得这是特别亲密的事。我不想把我的敏感暴露出来。比如突然的颤抖,一脸的眼泪,会让我难为情。我宁愿一个人去看场电影,这时身体的抖动,哭起来,都不要紧,那只是我自己的感受。电影院里的音效太响,总让我提心吊胆。坐在那里,光线是昏暗的,如果身边是可以信赖的人,那有多好,我可以放心地当胆小鬼。你是不是又笑话我了?春航于是正色道,没有,可能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害怕的东西。于是青瓦再一次撒娇道,我要你陪我看电影,或者去看戏。春航说,好。青瓦又要抒情,说,跟你一起坐在黑暗中,我觉得很安心。我要一直靠着你,还要一直握着你的手。春航说,好。青瓦问,你害怕过吗?春航讲,肯定有,只是我现在还不确定,比如,怕某种不可预知的命运,怕自己看不见却存在的东西。
青瓦说,你怕老吗?春航讲,我想人人都怕老,男人女人都一样,连皇帝都怕,所以秦始皇派徐福去找长生不老药,宁国府的贾敬吃丹药吃死了。女人怕容貌的衰老,男人怕哪天自己不行了。青瓦说,好像现在有一些男人,还不到四十岁,就喊自己阳痿了,说女孩子们可以跟他们玩,还不必防备把她们搞上床。春航笑道,就跟女人明明不胖却喊着要减肥一样的道理吧,男人都希望到八十岁还很坚挺,还能战斗。青瓦说,我真的觉得很多男人看起来都很疲沓。我感觉整天不断有人来你这里寻找力量,而你自己却感到衰竭。同情在衰竭,爱也在衰竭。春航讲,很疲惫的男人吗?我就是。想起那个过劳死的朋友,我也觉得害怕,好人没有好报。你知道我朋友人挺好,可是这么早就累死了,肝癌晚期。我明天去参加葬礼。青瓦担心地说,可是你来不及,没有直达航班。春航讲,我知道来不及,可是我特别想去送一程,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很难得。青瓦急道,反正你来不及,如果你明天下午才赶到,告别仪式已经完了,你也等于没去,不如默默送行吧。春航想了想说,也许只能这样了,一个好人,唉,这几年,每次见到我这个朋友,见他明显衰老下来,四十出头的男人,看着好像有五十岁。看来是得悠着点。
青瓦说,男人家嘛,不要把自己当精英才好。这个世界其实不一定需要你,我却是真的需要你。春航答应着。青瓦又说,你的身体表面上强壮,看起来比同年龄的男人年轻,可我知道你又是脆弱的,你很容易就感冒;有时候是易折的,你的身体很像在高速运动中的运动员,很容易受硬伤,不是吗?春航叹息道,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小时候暑假,有次我跟爸妈去杭州,灵隐寺边上有个算命先生说,你家小子命有华盖,却无官星,不出家的话,长大必有大难。记得我生那场大病时,有种顺从自然、无为而为的心态,既不抗争,也不放弃。有段时间在家养病,下午我会一个人走进兰心大戏院,看一场京剧,到黄昏就混迹在浩浩荡荡的下班人群中回家,好像我也下班了,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青瓦有些激动地说,要是那时候我可以陪你去看戏该多好。真遗憾那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春航讲,现在也不晚,我们不算老,再说,老了也可以看戏。青瓦又说,我害怕哪一天,我老得都不好意思在你面前撒娇,也不敢在你面前脱衣服了。春航就跟青瓦开玩笑说,你还怕更年期是不是?你放心,等到那一天,我只会比你更老的,我一样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脱掉衣服了。两只十足瘪三,我们在脱掉衣服前先关灯吧。青瓦说,我看到过衰老男人的光屁股,哈哈,真倒胃口,绝对像世界末日,再有钱有权,也避免不了那样一个可怜的老屁股。青瓦停顿一下,怕吓到春航,连忙解释,是在医院里。你说男人是不是从屁股开始变老的?春航诚实讲,男人应该是从下半身开始变老的吧。青瓦就说,女人的衰老是从眼睛的皱纹开始的。先关灯,这是个好主意。在黑暗中,你不顾一切地摸我,我不顾一切地摸你。反正有人说过,女人关了灯全都一个样。说着青瓦自己就开心地笑起来,又说,我从不用眼霜,反正一样是要老掉的。春航讲,记得你说过,我们是第一流的意淫高手。
电话断了,青瓦才发了会儿呆,整了整身上白色丝绸长睡衣的皱褶,春航的电话又打来了,说,你今天兴致好,接着讲故事。青瓦说,我还怕打仗、逃难什么的。那时候你会和你的家人一起逃难,我和我的,我们顾不上对方。如果手机还能打得通,最多只能打个电话问问,喂喂,你在哪里了。可是有什么用呢,和你一起同甘共苦的人不是我。
一个沉默,一个继续说。青瓦说,我看到一句“深锁春光一院愁”,就怕世事无常。还有世界末日,反正那一天我们不会在一起,所以我害怕我在这世界上留下最后的遗憾,就是死之前那会儿,你不在我身边,这太孤单了,一想到这,我就很失落。这时春航讲,我们活不到末日的那一天。青瓦说,还有我怕等我们很老了,身体很差了,也坐不动火车了,开不动汽车了,我肯定就见不到你了。春航讲,那也不一定。我们可以打电话,像现在这样,你想说多久就说多久。青瓦说,我还害怕,忽然有一天你又走了,移民去哪儿了,再不回来啦。春航知她心病,忙道,我不会再走了,亲爱的。又问,你今天为什么很悲观?青瓦说,我又发梦了。其实我并没有说真正怕的东西。我本来就是个悲观主义者,生命归根结底是悲的。春航讲,我说过,我希望你快乐,我想让你快乐。青瓦说,我现在闭上眼睛了。春航看一下表,说,很晚了,现在是凌晨1点,要不我们睡觉?青瓦说,我们睡觉吧,晚安。
挂了电话,青瓦发觉自己耳鸣的毛病又犯了,就睁开眼睛。睡不好,又发了好一会儿呆。青瓦想,这真是个话多的晚上啊。
前言/序言
后记
十多年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继续向左》,我写了一个都市小资群体,有点轻浮,有点迷惘,有点做梦,有点感伤,有点不负责任,不过基本上出不了穷凶极恶的事。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资们,基本上都妥妥地成为城市主流的中产阶级,这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和城市化是一致的。还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庆幸他们靠着个人奋斗和知识储备,没有在中国转型期从小资坠入到底层。这个中产阶层,除了压力,还有一些对生活的要求,或者说趣味,或者说乏味。如此,这是一个好的时代,是一个很多普通家庭子弟靠个人奋斗进了“985工程”大学,慢慢有了小资趣味,进而又成了中产阶级的时代。
趣味这种事,只有在不那么紧张的、你死我活的环境中,才有产生的可能。我读过很多很多的当下中国小说,发现讲生死的很多,讲乡土中国的很多,讲钩心斗角的很多,讲城市生活的不多,讲点趣味的,更少。
也许我看过太多的国外文艺电影,中毒了,心想讲趣味就有毛病吗?人家清少纳言一千多年前就讲趣味,到了20世纪的中国人还不配讲趣味?只有欧洲和美国才可以有中产阶级堂而皇之的生活方式和趣味标签吗?
写完这本书,我自己先审阅一番,本书只出现男主人公的发小作为罪犯死于严打,男主人公的同事过劳死了,其他没有谁彻底破产了或发疯了,甚至女主人公涉足的房地产业也没有人跳楼,果然是平淡得很。有一点职场里的钩心斗角,但也并不惊心动魄,只在日常范围,不构成强烈戏剧冲突。倒是有一群睡不着觉的人,虽然已经跻身在中产阶级了,但依然睡不好,因为心里总是有纠结,总是在该睡眠的时间里,东想西想,静不下来。可以说我知道的身边的职场故事和房地产故事要惊心动魄得多,也要丑陋得多,但我并不想写,因为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特别在乎的是那一种日常性。
“看月亮”是小资趣味的残余,“睡不着”就是中产阶级的当下了。在“看月亮和“睡不着”之间遭际的爱情,就成就了小说里中产阶级男女的爱情。在任何阶层,爱情都是奢侈品,对中产阶级也不例外。
曾经有一个朋友,现在早就失联了,以前在博客上读他的东西有一年以上,却从不知道他身处何地,只知道他在我们自己的国度。从他的每一幅图像和每一篇文字里,都看不出他具体的地点。不知他所居的省份的名称,城市的名称。只有他身处的那个特定的环境被放大,而那个特定的环境是一个现代的世外桃源。没有车马的喧嚣,没有俗世俗情的纷扰。只有很多的静物,一花,一草,一室。阳光,绿萝,桌子。从冬到夏,身外的世界被隐没,而自我被无限度地观照,放大。每一天的,或者同一天的好几个时间段的注视,细微处的体察,变化也在细微之间。如道林·格雷专注于自己的画像,每一次心灵的变化,使自我的画像发生怎样的变化?一丝游离,一丝忧郁,一丝愤恨,或一丝残忍?
这是一个非常专注于自我的人,我猜想他一定是王尔德的精神契合者,专注于解读自我、本我与超我。你想象不出外部世界对他的干扰值是多少。另一方面,你知道他除了艺术生活外,还有日常生活,他有很小的孩子,他需要打理他的家庭,还有亲情。显然他活在双重生活里。有一次,他非常温暖地祝福我孩子的生日,就像一个飘浮于云端的人忽然来到地面,我便出于好奇心,问这个来到地上的人,居于何处,而他的回答依然是一个抽象的回答。
于是我不再猜测,因为那没有多少意义。一个艺术家有他一贯的处世姿态,他愿意以抽象的眼睛看待地点和空间,我便尊重他的回答,不再追问。他只要忠实于自己,便是一个内心有坚持的人。再说,一个具体的地点,和一个抽象的只描写特征的地点,区别又在哪里呢?
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也开始思考空间的问题。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是普通的卧室与街道,房子,地铁,相似的风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重时间里。
我想到这个人对于地点的态度,原来,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待空间。人在各个空间,国度与国度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街道与街道之间,完成各种人类的行为。在构架各种地点的时候,我再次想到那位艺术家,只执着于跟小我有关的小空间,而淡化更大的地理空间——其实,更大的地理空间放到宇宙上,也只是极小的一个点。于是,人的行为也在一定意义上抽离于现实,有了超现实意味。
有些让我非常容易陷入的影像,看了一遍便束之高阁,因为第一次的冲击总是非常忠实地刻录于心头,我往往会害怕第二遍的具体化而回避它。比如克里斯·马克的实验影像。在那些非常有实验性的音乐背景之中,地点完全成为灵魂的外在影像,而不是具体的、真实的地点。岛,陆地,海边的城市,堤岸,那些地点完全被不同时间游走的观念和寓言所覆盖。
除了一个在特定的时间给人物打上深刻的灵魂烙印的地点,比如童年时的地点,故乡,其他的地点都模糊成一片,那只是城与乡,城与镇,大城与小城,中心与边地的区别。
大都市里的生活,大都市里的情感,甚至不同国度的大都市里的生活,正在趋于大同。我的身边大都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在信息发达到令人恐怖的时代,一种观念,一个说法,时尚潮流,一个词,一种疾病,一种情绪,与人沟通的方式,表达爱情的方式,欲望的产生与释放,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也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迅速蔓延。而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只剩下大都市与小城镇、乡村的区别,甚至连这种区别,都被冲击得体无完肤。这种现代性的入侵,使人自己的内心能保持的独立内容越来越少,而保留独立性的愿望也越来越少。
我有时会闷闷地想,真是平淡无奇啊,为什么大家活得差不多一样呢?很少有异人出现。在都市里,个体,正慢慢地被消灭呢。
我的小说里也是些平庸的人和事,生活被打回原形时,平庸的一面便一览无余。我不是一个热衷于挖掘罪恶的人,因为我认识的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是偏善的。当没有罪恶发生,也没有英雄辈出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看待生活,看待我们内心的追求呢?
在平庸生活的大背景下,我总想找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藏在人心里的一些顽固的东西——坚持,以及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世俗的超越——话说回来,一些虚构的人物总是比那些我们可见的现实生活中的交谈者更有鲜亮的色彩。
所以小说的开头就成了这样:“有一天,青瓦和五岁的女儿未央一直在翻米罗的画册,未央指着一幅画,高兴地说,妈妈,我要爬这个梯子,爬到月亮上去。米罗的画的确很有趣,画中有长长的梯子和大大的月亮,可是青瓦却觉得,那个特别想借着梯子爬到月亮上去的人,是春航。”
写作者的态度,真是开门见山,如此坦白了:仿佛平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恶”。
所以我说,中产阶级依然要看月亮。“看”是那个关键性的动词。相距一千公里的两座城市,两个人,也许就在很相像的小区,甚至同名的小区里生活着,一个九楼,一个十楼。某一瞬间,其中一个可能会恍惚地说,我就住在你的楼下。刹那间,那一千公里恍如不复存在。那样,他们就可以一起看月亮了。
小说的男主人公春航,是一个庸人,另一个角度上也是个“异人”,仿佛是被看不见的命运选中的生活体验者。他拥有各种类型的男女关系体验,生死临界点的体验,偶然与必然的体验,他乡与故乡心理差异的体验,亲厚的婚姻与深入的爱情的体验,从内脏到皮肉到关节的各种类型的身体疾痛的体验,以及囚禁与挣脱的内心体验。所以从某种角度说,男主人公是一个“异人”,生命给予了他不同质地的光彩和疼痛,也使一段又一段的长谈有了丰富的内容。对于爱着他的青瓦来说,他存在的意义就像一个凡人版的奥德修斯,他是个无畏的骑士,也是个怯弱的男人,所以,他们有了一段似乎会完结又似乎不会完结的旅程。
起先,小说里的主要地点是抽象的,用了我喜欢的名字:罗浮、香蜜,我也不知道从何处捡到这两个地名。我想要在一种长谈的氛围中,努力去接近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最后,我让食和色,人们通常说的最重要的人之“性”渐渐淡出,退后,直至禁欲,让位于特定的男人和女人将彼此当成心灵交流对象的持续的倾谈,直到这种挖井一般的长谈氛围,导致主人公虚脱了似的精神疲惫,然后,必将一方离开,然后,也有可能,回归,归于平淡如水。他们的确在一起看了很久的月亮,年复一年,但他们也终于不想再一直抬头看月亮了。因为总是有个现实,是他们无法回避的。
人总是在驱逐孤独和享受孤独中,在渴求和厌倦中摇摆不定,连爱情都不能改变。
人存在的本质是记忆。没有记忆,还会剩下什么?而记忆,总是需要填补新的内容。
确实,这部小说是我在儿童时代就一直在构建的乌托邦,有一段青年时期,我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古琴,看古书。我受了魏晋式清谈的毒害,毒液渗入体内,虽然与老庄无关,却成全了我对人生的态度和世界的看法,以及接近完美的男女关系的看法。我一直需要一个谈话的对手,幸好,我在小说中找到了。
时常认为,人有时要让自己变得高级一点,终究得淡化食与色的欲望。这仿佛是跟甘地等圣人的苦修理念相唱和,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悟到,但毕竟肉身常常缺乏亲身实践的动力和恒心,受各种欲望的驱使和奴役。而且,精神的对手是很难寻觅到的,对手的缺席,就造成了更多内心空茫的芸芸众生在欲望的洪流中翻滚,倍尝欢喜与痛苦。
孤独,寻觅,沟通,疲惫,离开,重回孤独,回归,沟通,疲惫,再次离开……就是这样的轮回,直至生命的尽头。
我看了一部电影。一个男人说,他们制作了一首歌,一首关于河流的歌。在望远镜里,他看到烟波微茫的河,河上有船驶过。
她问,你感受到了吗?
他说,什么,是河流还是歌词?
她说,两个都是,两个是一体的。
一个心里有一条河流淌着的人,说的是我,还是我正在寻找的?
我听到一句话:“河流才是人类生活的目击者。”我想河流不仅是目击者,还有芳菲的心,气味,音乐,哲学。最近我总是惦记着河流,惦记它流淌时的姿态,那种内在的律动,是我想要的,在寻找的。一条河的流淌,既不过于急促,也不过于缓慢。
我在寻找自己的节奏,但对自己却不甚满意。在这种不满意下,我其实一个字也不想写。
但我还是写了。小说先在《钟山》长篇小说增刊上发表时,最重要的地点仍是虚构的罗浮和香蜜,可能是因为两个不存在的地名,我依然有一种虚空缥缈的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是抓不住的,连故事也浮起在半空中,落不到地上,不能抵达某一个核心。于是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我们不该强调大都市中的同质化,而是应该在差异中找到自我的位置,也许有了真实的地名,这部长篇小说又会呈现出新的地域质感来?于是修订版中,我去掉了虚构地名,将小说主要地点改为上海、杭州和苏州,此三地是我生活过或在梦中时常出现的江南,如今在一个故事里,它们汇到了一起。
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是我任性地、反复折腾的产物,对我而言,它是具有实验性的。我在语言、对话、节奏、文本诸方面是算计了又算计,只可惜那个算计的人不是黄蓉,只是有一腔好奇心的萧耳。
我一直在给小说取名字,最初它叫“长谈”,后来叫过“清唱”“清唱或感伤”“亲爱的时光”“他的膝盖”“返光回照的青春”“轻如羽毛”“羽毛的优雅”“河流的名字”“玫瑰会枯萎吗”“自君别后”,现在是“中产阶级看月亮”,反正,一部小说,虽然作者花了心血,但它肯定有自己的命运。
最后要表白的对象实在太多,格非和他夫人是小说最早的读者,专门写信来对小说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程永新和贾梦玮两位中国文坛的“天才捕手”对我多有鼓励和促进,也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小说二稿终于在《钟山》上发表。还有同在杭州的作家艾伟和吴玄的热心,使《中产阶级看月亮》在出版单行本前就有了隆重的作品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重量级评论家为我的小说把脉会诊,令我受宠若惊。我在各地的女朋友——半夏、念青、王音洁、苏七七、陈江等,她们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喜欢这部小说,或者小说有打动她们的地方。更戏剧性的是,因为这部长篇,我在老浙大中文系(浙大、杭大合并后成了国文系)的系群里成了“一日网红”,如今早已在各种行业成为中坚力量的师兄弟姐妹们,被我的小说惹动文学情怀……
羞愧之余,我暗想,我得尽我的全力,拿出一个更好的版本来。
这也是对自1998年以来就开始的我的小说生涯的一个交代。女人写作,尤其写长篇需要聚气,中间很容易被种种尘事打断、消磨,几乎隔笔,但只要那颗以文字来抵抗红尘的心不死,总有一天,那个写作的女人会带着点沧桑回来。
萧耳
2018年5月15日晚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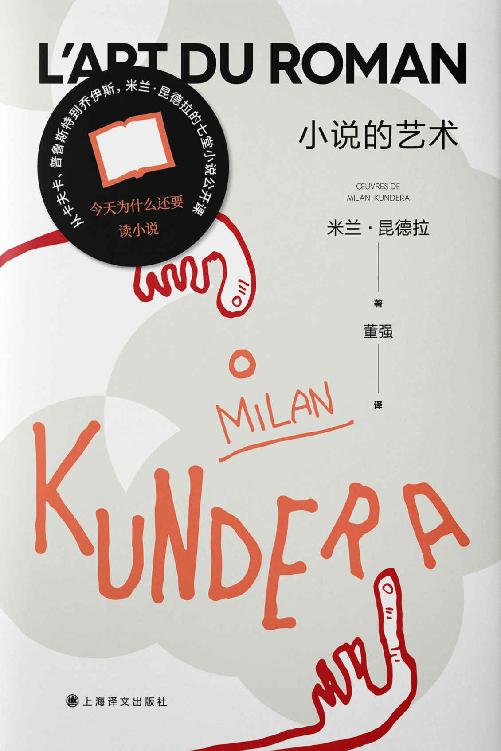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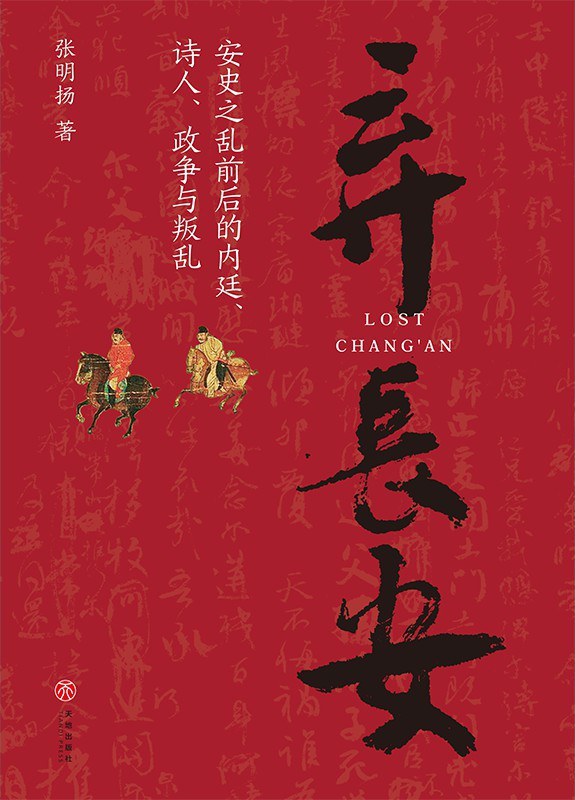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