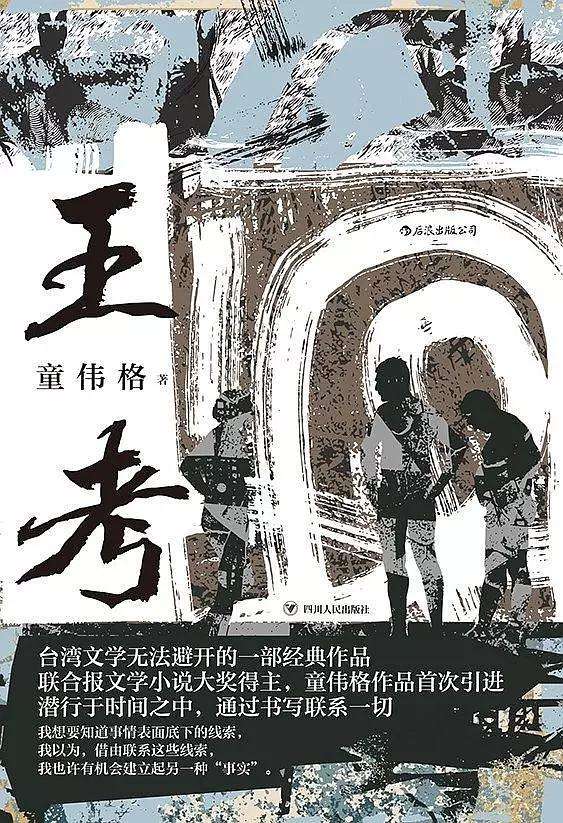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童伟格运用乡土、魔幻写实,甚至是历史与神话的嫁接等各种自由的叙事,拓展出九篇面貌繁复的作品,并在这些篇章以滨海山村为原点,反复书写来去其中的人。他们跨过山,越过海,穿行公路,去往城市,最终又回返山村。不断徘徊的人们,重复出现的场景,让小说展示出一幅幅时间冻结的画面,并且在一次次静止的瞬间之中,直面命运。
编辑推荐
☆ 童伟格是台湾六年级小说家中zuiju代表性的一位,曾获台湾省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台湾文学金典奖等认可,被认为是袁哲生、骆以军之后“内向世代的集大成者”。
☆ 魔幻写实、乡土主义、现代主义、内向世代……我们能从童伟格的书写轮廓中瞥见许多风格,却无法用某一个特定的形容词去概括他。如同骆以军所说:“童伟格的可怕,在于他可以解释其他全部人,而竟无人能解释他。”
☆ 作为童伟格首次引进的作品,《王考》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童伟格25岁出版的首部作品,一出版便惊艳台湾文坛,在其中他将种种小说的技艺操练到相当的高度,如黄锦树曾言:“童伟格的小说写作,几乎是一开始就很成熟了,好似直接跳过了学徒的阶段,第一部小说集《王考》里的多个短篇就几乎是杰作。”
☆ “我问祖父,爱情是什么?我问他,人怎么这么愚蠢?我问,我们活着为什么?”在《王考》中,童伟格用锐利的冷调文字捕捉生命中的神秘瞬间,讲述老灵魂不欢的童年故事。他拆解具体情节、冻结叙事时光,让人物直接和命运对话。故事仓皇流转,却始终覆盖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精彩书评
☆ 我确实为童伟格这些篇优美纯粹的小说迷惑吸引。“怎么可能那么好?”那是一个比我的小说启蒙时刻上跳了几十年的,宽阔而完整的“人直接与命运对话”“叙事尚未被污染之前”的地貌。
——台湾小说家 骆以军
☆ 《王考》彻底的抒情风格,也道出童伟格与抒情主义的亲缘性。在这一点上,他的写作可说是位于其他两个早夭的同代人袁哲生(强烈的抒情性)和黄国峻(标准的现代主义)的延长线上,企图更远地朝向其消失点——那永远不可能趋近的可能性的尽头。
——马华文学作家 黄锦树
☆ 老灵魂不欢的童年,这是我对童伟格的小说看法。他几乎用小孩“我”的口吻说故事,锐利而冷静,情节流畅,难得之处是他擅用人物的动作描摹内心状态,纯然带着说故事的本色。读他的小说,我想到的画面是:“乡村杂货店前的老人,讲着童年故事。”
——台湾小说家 甘耀明
☆ 在《王考》这本小说中,处处充满了死亡与失落的阴影,仿佛是不可抗拒地陷入到一个时间与时间的夹缝之中,指针卡住,故人物仓皇流转在梦境与现实的边际,而生与死俨然成为一体之两面,记忆斑驳成为拼凑的残缺碎片。
——台湾作家 郝誉翔
获奖记录
☆ 《我》荣获1999年“台北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
☆ 《暗影》荣获2000年“大专学生文学奖”短篇小说叁奖
☆ 《躲》荣获2000年“台湾省文学奖”短篇小说优选
☆ 《王考》荣获2002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
☆ 作者以长篇小说《西北雨》成为2010年“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得主
目录
5 王考
23 叫魂
45 我
59 假日
71 发财
79 暗影
95 躲
117 离
131 驩虞
179 【附录】暗室里的对话
精彩书摘
关于我祖父如何在一夕之间,成为人人惧怕的怪物,据亲历其境的我祖舅公追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本乡三村——海村、埔村及山村——村人,难得一起聚财聚力,翻山越岭十数回,终于由城内尖顶圣王本庙,求出圣王正身一尊,当时迎驾北归的父老们感觉自己,敢比执得鞭随了镫的周仓爷——真个死亦甘愿。然而,车驾甫出城界,到了尪子上天山脚下的冷水堀停息未久,父老间就起了争端,原来,三村都各自建好了圣王庙,谁也不愿在轮流供奉的次序,及供奉时间的短长上退让。
祖舅公说,海村多的是手操蟒舟、越海岬至东岸运米、竟日来回大气不喘的勇士,埔村的人,则是大刀王简九头的后裔,男女老少身上绑着两百六十斤重的武练石去耕作担水,全然不当一回事,果真让这两村的人占了先,到时他们困着圣王、食言不还,我们拿什么去和他们拼命?
祖舅公当时在冷水堀的湿地上站了半天,站到人都快陷进地底矿坑里了,依旧无法可解,心中很觉凄楚。眼见磨刀霍霍的诸村精英,他想,若果然又起械斗,山村仍是毫无胜算,几十年间,山村村人为后进所迫,让出海岸、让出平原,搀老扶弱进了山地,犹能保有一线生机,如今,恐怕为了千百年前的圣王老祖宗,要彻底肝脑涂地了。
头顶的尪子上天山,山顶蒸腾的雾气摄入更高的雨云之中,祖舅公说,当时他想起他的妹婿——我祖父——告诉过他,这座本乡境内最高的山,山名的由来,是因为山顶的磺雾氤氤直上,第一个看见的人,错觉有人影上天,故名之。祖舅公听祖父这样说时,曾问祖父,那第一个人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祖父凛然,从书架搬下一大部旧书,剥开书页,用细长的指甲指了斗大的几行字,要祖舅公自己读,祖舅公看得了“日”,看得“雨”,看得“水”“花”“秋”与“冬”,但整段字看得不知伊于胡底,他只惊奇,那些蛮荒不明的事,怎么,我祖父看书就知道了?
接着,祖舅公做了一个后来他“连做梦都在后悔”的决定,他用力提起半只已陷入泥地里的脚,呼吁三村壮士,用文明人的方式,谈判解决这件事,暗地里,他派人快去接祖父来,做山村的全权谈判代表。
圣王是我们的啦!祖舅公说,当他看见凤嘴银牙的祖父,在众人的簇拥下,目光炯炯走上坡时,心中忍不住这样欢呼,他淌着泪,急急迎上我祖父,握着他的手,喊着,辛苦了,辛苦了,这一趟真不容易啊!
祖父止住了祖舅公,他用那双刚从书案上移开的双眼,审视在坡地上、在堀坑旁横七竖八躺着的三村村人。高处,一尊黑木刻的神像端坐轿上,浑身穿戴金碧圣衣,像一具被火烧焦、又被人郑重弃之的婴儿尸骸,座位两旁,摆着令旗、令刀,与一袱黄巾包妥的小物事。
这就是祂了!小心,手脚轻点!当祖父开始熟练地考察、翻检着圣王时,祖舅公在他身旁候着,喃喃碎舌。祖父面色凝重,不发一语,最后,当他打开黄巾,翻出圣王印时,呜,他沉吟了一声,细细检视完印上的字后,他抬头,高兴地对祖舅公说,只有这印是真的。
都是真的啊!祖舅公摊开双手,像要给祖父一个拥抱。
祖父又止住了他。据祖舅公说,后来祖父拿着圣王印,招招手,开始了谈判会议,会议中,祖父不容众人激辩,甚至不让人打断,从午前径自说到了傍晚。祖舅公抹抹老挂到下巴上的眼泪,只觉得,身旁众人为了祖父的话,时而笑、时而哭、时而怒号、时而安静,到了黑暗逐渐沉落的时候,众人居然一派和谐,满面红光,宛如圣王亲临。
祖父止住演说。片刻后,一声吼,两面光,三村村人就地拔起,当场分了圣王老祖宗。埔村大刀王的后裔,夺了令刀、令旗与圣衣,扬长而去;海村勇士扶得轿子,将光头裸肚的圣王高高架起,欢呼下坡;只剩下山村村人,呆看着祖父手捏着圣王印,像捏着一枚卵蛋,就着一天中最后的余光,独自鉴赏着。
夜里,亲临分尸现场的山村村人睡不安稳,愈想愈怕,他们怕神、怕灵,也怕祖父。第二天,他们集合,互贾余勇,把圣王印从祖父的书房抢了出来,之后,他们到木匠家拜访,想求木匠补刻一尊圣王像,去了才知道,木匠昨天夜里就被埔村人,用几十把刀架走了,于是,他们绑回了木材,和木匠的老婆。
更大、更真、衣着更辉煌的圣王像,总算造成了,连着圣王印,经年供奉在庙。从此,山村村人总避着我祖父,只有在心有所求,求之圣王而不应时,他们才会暗暗想起他。
想起他时,他们就编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有人说,祖父有四根舌头,所以会讲四种语言,和他相处久了,你连爹娘是谁都会忘记。还有人说,一生连让我祖母怀孕当天,都没有离开过书案的祖父,书房里还藏了几副备用的家伙,是以,猪瘟横行的那几年,我们家还有闲人闲情,翻修总是漏水的猪舍屋顶。
久而久之,“人畜兴旺”在山村,成了一句严重的粗话。
相反地,事实很快就湮灭在激动的情绪里,为人所遗忘了。祖舅公风吹人倒、行将就木的最后那几年,我总是随侍在侧,一抓着机会,我就抽出速记本,细问祖舅公,那一天,在我印象中向来倔傲沉默的祖父,究竟说了什么,能让三村故旧如此痴迷。躺在病床上的祖舅公,只是眼泪直掉,他说得了“磺气”,说得“东风”,说得“芒草”“金针”“裸猪”与“瓜屎”,但终段不成一语。
有几次,祖舅公甚至将我错认成祖父,激动得昏死过去。
今天清早,我收完蟹篓,刚爬出溪谷,远远地就看见我祖父站在马路边。我走上前,发现他穿着我父亲的雨衣、雨鞋,两手环抱我家厨房那一大瓮红砂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喘着气,兴致奇好地回答我说,他要去看海,原本打算沿着公路下山,一直步行到海边,但刚出村口他就累了,所以姑且在此站一会,且休息、且等公车。我打量四周,想起了几十年前,这里的确建有一处候车的小亭子,只是后来乘客少了,原本一两个钟头来山村一趟的公车早取消了,小亭子和公车站牌,也都不知拆去多久了。
我知道,真正的终局就要到来了。
终局之前,唯一不变的是,处于公路终点的山村总是在下雨,并不是爽快的倾盆大雨,而是一种从各个物体表面每时每刻不断渗出的毛毛细雨——狗身上下狗毛雨、猫下猫毛雨,山村里的小孩都长大成人,离开山村了,他们婴儿时代的衣物,还挂在檐下干不了。
我问祖父,累了吗?祖父摇摇头,继续静立雨中,闭目养神。汗水浸透他的长衫,贴住了雨衣,我放下水桶,靠着护栏坐在马路上,等祖父逐渐调稳呼吸。背后溪流湍湍,鸟鸣声逐渐安静,四周更亮了一点,太阳应该已经完全升起了。此时山村内,三三两两醒过来的人,必定把软软重重的衣服,从压弯的竹竿上摘下来,套在身上,带几瓶酒,开始往门前那棵公共大榕树走去。
榕树底,有一顶石棉瓦与木柱搭起的大棚子,卡拉OK大风行的那几年,大家合作,在棚子里架了卡拉OK,后来流行有线电视,他们也翻山越岭把电视缆线牵进棚子底。长久失业的村人,日复一日聚在里面喝酒、赌博、争是非、闹选举,一年中总有几回,他们会劳动分驻所几位衣衫不整的警员,开着警笛故障的巡逻车,前来树下关切一番,但大致上,并没有闹过什么大事,他们只是喜欢一起挤在棚子里,像几团浸在水里的棉花。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潮湿的棉花人,从我的父执长者,逐渐变成了我的同辈友伴。
童年时,我总是光着脚,和同伴在雨中跑来跑去。我们从家里偷出筷子,在沙地上挖洞,看着地底喷泉泌泌泌泌涌出,我们用罐子抓沟渠里的长臂虾、软壳蟹,把它们一只一只放进水田里,或者,我们从口袋掏出、从身上搓出、从地上抠出一团又一团的烂泥巴球,往三合院的猪舍里甩去,等祖父出来喊我们。
每一次,祖父都会从猪舍旁的书房走出来,在门口站好,招招手,用细细的哭腔对我们喊,快进来,不怕着凉吗?他向来慢条斯理的,但从他的神情,我们知道他真的着急了。我们不理他,继续对书房和公厕中间的猪舍丢泥巴球,阴暗的猪舍里,猪倒抽鼻子发出抗议声,我们乐得哈哈大笑。
在那个被满山遍野菅芒、赤竹、榕树与姑婆芋环抱的三合院落,祖父站在房舍末端,满眼满眼都是泥巴,书房门口、他的头上,挂着一个木头匾额,旁边,几头大猪疯狂地吼叫。泥巴地里,几个小毛头指着匾额问他,爷爷,上面写什么字?
祖父一字一字回答,养、志、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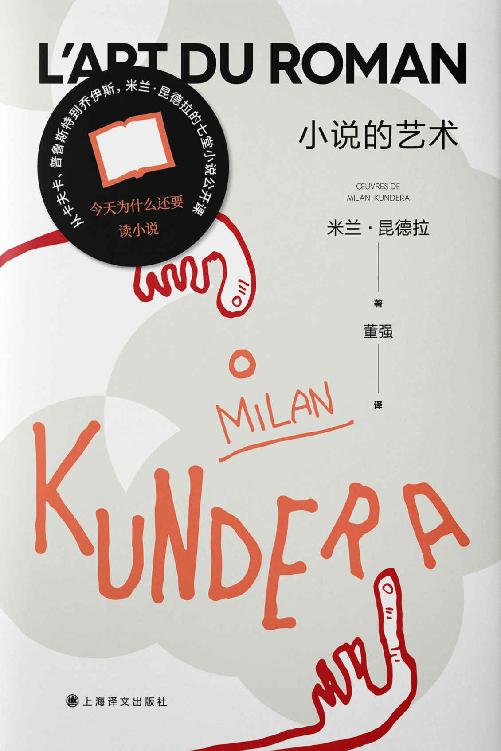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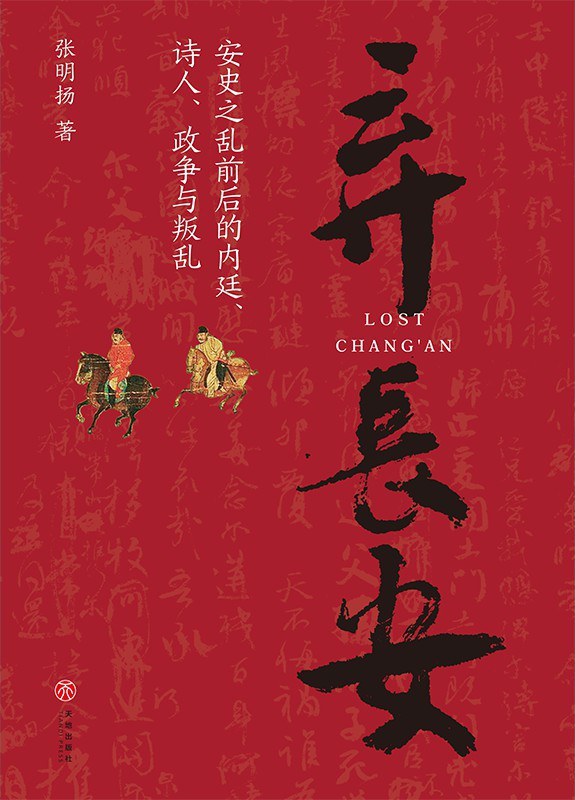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