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治维新不只是全面现代化的政治革命,也是日本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时刻。处于时代的锐变中,武士家族的女孩们能否接受未来的挑战?她们又如何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景观?
《武士的女儿》讲述了日本三位著名女性教育先驱山川舍松、津田梅子和永井繁子的传奇经历,通过女性地位和命运的变迁,展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的深刻转折。
1891年,三人作为明治政府北海道开拓使选派的留学生随岩仓使团前往美国留学。她们的使命是学习西方的文化和规则,学成后归国协助培养将要领导国家的新一代开明日本人。她们都生长于动荡时期的武士家族,作为日本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一到美国,她们立刻成了名人。留学期间寄宿于美国家庭,完成学业,成为典型的美国女学生,和当地人结下了友谊。 十年后,她们学成返回日本,决心在已成为陌生异地的家乡,掀起女性教育的革命。山川舍松推动日本外交,协助创立日本红十字会,津田梅子创立日本知名学府津田塾大学,永井繁子也成为当时知名的教育家。
作者简介
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Janice P. Nimura),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美国作家、书评人,日本媳妇,在日本生活多年,研究领域:东亚史,日本史。
精彩书评
1. 二村用其优美的文笔巧妙地编织出三位女孩迥异个性,犹如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
——Christopher Benfey, 《纽约书评》
2.《武士的女儿》的真实故事读起来如小说:三名女孩在命运的捉弄下离开故土,成为连接日本和美国的桥梁。作者以电影的笔触呈现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Authur Golden,《艺妓回忆录》作者
3.你很难找到能够游刃有余地刻画人物关系和人物内在思想的小说家……二村做到了!在本书中,她通过三位少女的故事切入讲述了大时代的变迁,成功地构建起日本和美国文化的桥梁。
——Becky Krystal, 《华盛顿邮报》
4.二村实现了很多历史学家们无法企及的成就,她的这部作品得到了学术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的青睐。作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叙述了三位女性的传奇经历,展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日本社会的图景。
——Miriam Kingsberg,《洛杉矶书评》
5.关于三位非凡女性的精彩绝伦的故事,敏锐地扑捉了现代社会中异质文化间的冲撞。《武士的女儿》是日本文化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一本历史著作。
——Ruth Ozeki,《不存在的女孩》作者
6. 通过历史与传记的迷人编织,作者讲述了日本面对现代化势不可挡浪潮中的生动故事——关于日本女性的教育和解放启蒙,独特而优雅。
——Kirkus Review
7. 作者书写了一部精致细腻的集体传记。传记爱好者、对美国镀金时代或日本明治维新感兴趣的读者,以及《艺妓回忆录》的书迷,将对其手手不释卷。
——Library Journal
8. 作者细心地串联起信件和档案文件,在这部关于日本内战后三位武士之女被送到美国的传记中,讲述了巾帼英雄的真实故事。
——Publisher Weekly
9. 本书对于这些文化遗孤和时代先锋者的描述如同小说一般精彩,让人动容。
——Julia Pierpont,《奥普拉杂志》
10. 读起来犹如小说,在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交融中,窥视三位非凡女性传奇的生命转折。
——Elizabeth Bennett,《达拉斯早报》
11. 本书记录了日本女性主义的萌芽,作者非凡的非虚构历史叙述技巧增强了整体的真实感。
——Historical Novel Society
目录
作者的话
第一部分
序言
第一章 武士的女儿
第二章 龙年的战争
第三章 面酵的力量
第四章 务实者的观察之旅
第二部分
第五章 有趣的陌生人
第六章 找一个家
第七章 像美国人一样长大
第八章 在瓦萨学院的日子
第九章 回家的路
第三部分
第十章 两场婚礼
第十一章 踽踽独行
第十二章 爱丽丝的到访
第十三章 进与退
第十四章 女子英学塾
第十五章 尾声
致谢
精彩书摘
务实者的观察之旅
岩仓使节团成员临行前,天皇特设国宴为各位送行。宴会间,天皇发表了一番非常诚实的讲话:“如果我国想要获益于文明国家实用的文化、科学和社会环境,我们要么在家里竭尽所能地学习,要么派一批合格而务实的观察者,在异国的土地上获取我国人民不具备、但经验证有益于我国的知识和能力。”施行明治维新的日本天皇,公开承认他的国家尚未获得文明。
“游历外国,适当地沉浸其中,能够增加一个人的实用知识储备。”天皇继续道。经历了250年的闭关锁国,日本人对探索国门以外的世界这一概念感到不适应——这是件彰显活力之事,但也似乎伴随着危险,就好像一杯烈酒,需要保守地品尝。“我国内部存在着严重弊病,急需治疗。”天皇这样说。天皇居然承认众神的国土有其弊病!然而天皇还说了其他的。“我国缺乏培养精英女性文化的高等机构。我国女性不应该对关系到生活康乐的重大原则如此无知。虽然我们正致力于设计发展一套针对民众的文明开化体系,但是,对后代教育起到早期培养关键作用的依旧是母亲的教育!”突然间,女性的幸福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目标层面。日本政府意识到,日本的文明开化进程是不能缺少女性的。
“因此,出行使节团成员的妻子和姐妹获准陪同,她们可以了解当地的女性教育,归国之后,将所获体验用于提升教育子女的水平。”天皇继续道。听了这番话,宴会席间围坐一桌的一些日本名流并未有所表示——虽然天皇的演讲稿出自他们其中的几位,但这些人并未对天皇的想法上心。后来,岩仓使节团的大使们没有一个携妻出访的。如果让女性学习外国人的那一套这么重要,那就让不用他们操心的其他男人的女儿们打头阵吧。
横滨码头上挤满了岩仓使节团代表们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中许多人此时的穿着比昨晚送别会上的穿着朴素了许多。女孩们身上的和服是未婚女性的式样,她们缓缓走上码头旁晃动的踏板,尽量不踩到及脚的和服下摆。横滨此时正值12月末,阳光依旧强烈,地面上却结着一层厚霜。看客们伸长了脖子,在人群中上下左右地争取找一个*佳位置,希望能看一眼这些日本*出名的政府官员。当他们看到竟有几个女孩也跟在使节团队伍里,使得整个队伍看起来有些不协调,纷纷表示惊讶。女孩们有些僵硬地走到遮篷下,坐在她们的监护人德隆女士身边,张望着码头上的人群,试图从中辨认出熟悉的面孔。使节团的其他成员登上了其他几艘小一点的船。
“这些女孩的父母有多狠心啊,”梅子的姑妈听到一个旁观者说,“竟然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美国那种野蛮的地方!”没有人反驳她。在场的一些人或许知道,这些女孩并不是第一批被送去美国的日本女性。会津战败后,普鲁士军火商、大名领主军事顾问约翰·亨利·施奈尔(John Henry Schell)曾带领一批会津武士、农民(包括施奈尔本人的日本妻子),携带茶籽和桑蚕,去往加利福尼亚。1869年6月,这些开拓者在萨克拉门托东部的普莱瑟维尔建立了若松茶叶与丝绸移民地,却很快败给了当地恶劣的气候,有的死去,有的挣扎在穷困之中。“这是一个奇迹,”梅子后来写道,“在日本历史上竟会有这样五个女孩的父母,同意让她们进行这项冒险的事业!”
似乎没人想到应该给这些即将在异国他乡生活十年的女孩们准备些实实在在用得着的东西。使节团的男性代表们设法找来一些西式服装,虽然不能引领时尚潮流,但好歹可以应付场面。许多代表还带了厚重的英文词典。女孩们两样都没有。女孩中唯独小梅子还算带了些在美国用得到的东西:一本注明罗马拼音的英文初级读本,一本《常见英文单词的日文对照口袋书》,一条和梅子身上的和服不怎么相衬的亮红色羊毛围巾。
梅子告诉姐姐们,这些是父亲津田森(Sen Tsuda)给她的礼物,从记事起,父亲就给梅子讲很多有关美国的事情。梅子骄傲地告诉大家,她的父亲懂英文,曾做过将军的翻译官,还去过旧金山,此次使节团的船也将要停靠在旧金山的港口。父亲从旧金山带回了很多参考书和手册,还一时兴起,把头上的顶髻减掉带回来了。梅子一直没有忘记母亲打开父亲的箱子时脸上目瞪口呆的表情。
美国之行改变了津田对待女子教育的态度。回家后,他坚持让梅子学习读写。那时梅子不过4岁,就从早到晚地上课。梅子是个聪明孩子,很快就学会了五十音图,之后开始学习以日文形式书写的中国象形文字——汉字。
与舍松的家庭一样,梅子家也在此前的斗争中成了失败的一方,失去了曾经为将军效力时的家族实力,她的父亲正在挣扎着重新立足。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如果有什么机会能够减少需要养活的家庭成员人数,梅子的父亲是愿意接受的。父亲心里明白,梅子还有两个弟弟继承家族香火,而梅子是可以被送出去的那个孩子。同时,梅子的父亲也认为,送女儿出国还有另一重好处。除了帮家里减轻财务负担之外,接受过美国教育的女儿回到日本后还能给他带来荣誉:如果女儿能讲流利的英文,又耳濡目染西方礼仪,那么将无疑能够帮助作为父亲的自己提升在新政府中的地位。
津田*初打算送大女儿琴子去留学,但是在*后一刻,琴子退缩了。于是家人决定让比琴子小两岁的梅子代替琴子去美国。梅子出生在1864年的*后一天。当她的父亲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时,得知刚刚降生的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儿,便大发雷霆。孩子出生第七天需要起名,但到了第七天,父亲还没回家。又因梅子母亲的床边有一株梅树盆景,所以就有了梅子这个名字。腊雪寒梅,梅代表了美与坚韧。现在,真正的考验就在眼前。不像琴子,一个月后才7岁的梅子并不懂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决定。那个叫作美国的遥远又陌生的国家,听起来就像是童话中的国度,梅子感到好奇。此时,她的英语水平也就仅仅停留在会讲“是”“不”和“谢谢”。
岩仓具视身着朝臣长袍,庄严地站在领头船的甲板上。领头船以蒸汽为动力,其他小船由水手划桨,紧随其后。小梅子的衣着非常醒目,火红的和服上绣着引吭高歌的仙鹤、菊花以及和她同名的梅花,五个女孩的小船滑出码头一段距离后,人们从岸上还能看到明丽的梅子。停泊在*远处的是太平洋蒸汽轮“亚美利加”号——全球*大明轮船之一:从船头到船尾363英尺(约111米),仅甲板面积就有一英亩(约4047平方米)。这一天,在美国星条旗的旁边,扬起了日本太阳旗。仪仗队鸣放19响礼炮,发射15发空弹,向即将出发的美国大使致以敬意。加农炮的浓烟飘过水面,回声在海港的上空久久萦绕。
100多名代表,以及他们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行李,都成功上了船。中午时分,当*后一声大炮轰隆响起,船锚浮出水面,巨大的桨轮开始转动。“亚美利加”号正式启航。“横滨码头停泊了许多外国船舰,我们经过时,船上的水手们纷纷收起缆绳,向我们脱帽致礼,”官方记录者久米邦武这样写道,“我们身后是绵延好几英里的船只,上面坐着为使节团送行的祝福者。”
使节团代表们高尚的理想很难被忽视,他们此行的目的便是要为日本的对外交流史打开一页新篇章。在使节团这样宏大的目标背景下,随行的这五个女孩似乎就很容易被忽视了。果不其然,久米邦武在官方记录中错将五个女孩记成了四个女孩。
海浪之上,富士山披着厚厚的雪袍,神圣庄严,从船上看去,壮丽的美景一览无余。“开船的时候,天气非常好,”两年后,初习写作的梅子在一篇英文作文中写道,“当我看到地平线一点点消失,我心跳加速!我试着不去想离开家这件事。”太阳落山后,游客们还留在甲板上,一直看向西边的天空和大海,直到海面被月光笼罩,美丽而安详。夜晚来临后开始起风,令人兴奋的夜景也因此逐渐模糊,船身也开始晃动。
三个星期的航行苦不堪言。隆冬时节的太平洋上暴风雨频发,五个女孩就蜷缩在狭小的船舱里。亮子和梅子睡在铺位上(因为梅子太娇小了,所以睡得下),繁子将行李架当作床。繁子的姐姐给了她一双草鞋,叮嘱她将草鞋放在枕头下面,这样就不会晕船。可是不管有没有草鞋,五个女孩都感到非常难受,她们卧床不起。
繁子的年龄比舍松小,比梅子大,她的人生历程也落在繁子和梅子之间的某个点上。和梅子一样,繁子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东京度过的,身边的哥哥和大人既对西方思想感兴趣,又保持着对将军的忠诚。她的父亲益田鹰之助(Takanosuke Masuda)是北方通商口岸函馆的行政官,函馆也是舍松之前居住过的那座城市。繁子的哥哥孝(Takashi)11岁开始学英文。繁子家1861年搬回江户,那一年,繁子刚出生。繁子还记得,她的父亲和十几岁的哥哥两年前随使节团访问欧洲。他们一路经上海、印度,过红海、地中海。繁子看到过一张合照,照片上大家头顶烈日,站在一尊头部巨大的石像——狮身人面像前。
和舍松一样,戊辰战争给繁子的旧生活画上了句号,迫使繁子与家人分隔两地。1868年7月,北部诸藩联合对抗尊皇派的进攻,战火也烧到了江户城堡以北,打破了繁子家附近小石川的平静。尽管南方诸藩已经攻占城堡,废黜将军,推年轻的明治复位,但部分佐幕派依旧没有放弃。前大将军手下的一千多人将大本营安在上野的一处寺庙里,这里距江户城堡不到一公里。孝举行婚礼的这天早上,尊皇派的军队穿着蓝色西式军服,头戴南方武士简陋的发髻,突袭上野。
一整天,繁子和家人听到的尽是炮弹嘶嘶和轰隆的声响。方圆几公里内的房屋化为火海,上空是浓浓的黑烟。新郎和其他男人们已经脱掉为婚礼准备的华贵服饰,抄起武器,匆忙奔赴战场。“新娘被抛下,和妈妈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繁子回忆,“朋友们都跑来了,为了躲避外面的炮弹,家里一阵骚乱。”夜晚,上野之战结束。将军势力*后的一丝坚持也被击溃。败军的头颅被挂在木杆上。繁子忘不掉那场面,“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夜晚”。
江户已乱,对曾经效忠将军的佐幕派来说,再继续待在这里会有危险。繁子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忠心耿耿地为将军效劳,所以她的家庭正在受到威胁。胜利的尊皇派士兵们游街欢呼,以骚扰曾经的德川幕府拥护者为乐。孝已经失去了两个幼年患病的姐姐了,他不想再失去第三个。为了保护繁子,他认为,*安全的方法就是把繁子送走。孝在为将军骑兵队服务时,认识了一个医生朋友永井玄荣(Gen’ei Nagai),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正要随其他被流放的将军随从离开东京。永井答应收养繁子,并把她带出动荡的首都。一切发生得是如此之快,繁子还未来得及消化眼前这一桩桩变化,她已经有了新姓氏、新家庭。一路摇摆颠簸,尘土飞扬,繁子整整坐了五天日式笼轿,到达东京西南的一个叫作三岛的地方。繁子在三岛的新家住了三年。
幸好在战胜方那边有孝的朋友,这位有身份地位的朋友帮孝在财政部谋得了一职。一听到招募女学生的消息,孝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他既没有通知妹妹,也没有通知寄养家庭,而是替妹妹做主,向北海道开拓会递交了申请。当信使从东京骑马而来将繁子需立刻启程赴美的消息通知给永井一家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10岁的繁子也震惊了。繁子已经在村里的寺庙学校上了三年学,会读写日文,但一个英文单词也不会。对于政府对她未来的安排和期待,繁子如何能够胜任?当孝递交申请时,他有预感,妹妹会同意。实际上,当时繁子的生活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养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苛,待繁子也从来没有亲近过。去美国这件事想想虽然有些害怕,但未知的将来有可能好过现在的境遇。对于自己将要和永井家说再见这件事,繁子并未难过。
在拥挤的船舱里,女孩们恶心了两天两夜。好心的送行人之前送给她们的几盒点心被塞在船舱顶部,让整个空间显得更狭小了。中国侍者端来辨认不出是什么的食物,她们实在不想尝试。监护人德隆女士不会讲日文,使节团里的男代表们,虽然有时候会好心帮她们做翻译,却也并不知道女孩们需要什么。身边的女侍只会说一句日语——“您需要什么?”但女孩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用英文回答她。当饥饿感比晕船的呕吐感更强烈时,她们只好取些点心充饥,然而这么做却只让她们更加感到不舒服。
第三天,隔壁船舱的一位代表来探望女孩们了。这位使节团代表叫福地源一郎(Gen’ichiro Fukuchi),福地是财政部官员,个子不高,为人坦率,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日本新闻业的领军人物。在此之前,参加过两次使节团出访活动,所以他非常清楚特使在船上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他走进女孩们的房间,看到五个女孩面色苍白,浑身湿冷,旁边放着只剩半盒的点心,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打开舷窗,抓起剩下的点心,扔出舷窗外。“我们怎么哭怎么求都没用,”繁子回忆说。
从这之后,女孩们还是没有出船舱。又过了一周,先是梅子觉得好些了。她沿着金属台阶走上甲板,看到高个子的美国水手,以及穿着帅气制服的美国军官,梅子感到惊讶不已。待女孩们纷纷都上了甲板,她们仔细地参观了一番:气派的酒吧和餐厅,轰隆作响的引擎,只有滚动着的明轮证明,船依旧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上前进。“乘客不得接近明轮工作区域或在甲板栏杆外走动,”女孩们读懂了船上的警告牌。“不要和工作中的军官讲话。”每天,船长会报告当日所到达的经度数,大使们会仔细记下,带表的人也会及时调整手表时间。
下雨,下雨,航行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大家在熟悉了整艘船的结构之后,就觉得没什么新奇的了。“我们连岛屿模模糊糊的轮廓都看不到,”使节团的记录官久米邦武这样写道,“虽然满月之日到了,但我们几乎看不到月亮,这加剧了大家的孤独感。”
正当女孩们还在为点心被福地扔出去而感到难过时,伊藤博文来看女孩们了。伊藤是高级大使,是福地的一位很亲密的朋友。伊藤身材矮小,但性格豪迈,虽出身卑微,但志向高远,他看上去自负、帅气、勇敢、懂得享受生活,笑的时候透出男孩般的快乐。22岁时,伊藤想方设法偷偷去英国留学,今年30岁的他,已是工部大臣。“他说如果我们表现好,就可以去他的房间,他会给我们一些好东西。”后来繁子回忆到。伊藤给了女孩们一人一点珍贵的味增腌咸菜,这家乡的滋味安抚了女孩们的胃和神经。这并不是伊藤*后一次出面改善女孩们的境遇。
船上无聊的生活让使节团代表们感到沉闷。岩仓使节团的成员们有野心、有抱负、骄傲,但缺乏安全感。享受到掌权后胜利滋味的南方诸藩武士们仍然认为,比起忠诚于彼此,他们更愿意忠诚于自己的藩地。那些曾效忠于大将军的人依旧满怀深深的仇恨。两方人马直到不久以前还是敌人,他们还在学习,如何成为同盟,如何完成将新政权介绍给外部世界的重大挑战。
那些出过国门的觉得自己比从没离开过日本的要高出一等。有一位使节团代表是司法部门的官员,他喜欢在西餐礼仪方面给大家做辅导:左手拿叉,右手拿刀,要把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而不是拿起一整块肉送进嘴里;吃东西不能出声。傲气的年轻代表们很讨厌好为人师这一套,吃东西时反而放任自己,弄出更大的声响。
在这群没什么事做而憋得发慌的男人中间出现了几个女孩子,这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某些程度上的兴奋感。女孩中年龄*大的亮子和悌子,都是14岁,几乎到了适婚年龄。直到返程回到日本之前,她们都是使节团男性们唯一能见到的日本女性。并不是每一位使团代表都像伊藤和福地那样亲切又不失得体。一天,一个叫长野岩仓使节团中有两个姓长野的人,也有学者认为对亮子有不当之举的是司法大辅佐佐木高行的秘书长野文炳,长野文炳来自南部藩地,更有可能欺负来自战败方家庭的女孩。同时,因为他与佐佐木的亲近关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佐佐木强烈反对举行模拟审讯。然而,在自己的记录中,佐佐木提到长野桂次郎和长野文炳(Fumiakira Nagano)时都以长野称呼,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是谁骚扰了亮子。——作者注的男人醉酒后,突然闯入了女孩们的船舱,这个人是外务部秘书。当时,船舱里只有亮子一个人,亮子奋力地躲避这个扑上来的男人。不一会儿,其他几个女孩们回来了,目睹了眼前的一切。愤怒的舍松赶紧跑去向大久保求助。
虽然使节团当中有两个叫长野的人,但长野桂次郎(Keijiro Nagano)更具嫌疑,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色之徒,此方面的劣迹也相当丰富。1860年,只有16岁的长野作为学徒翻译,参加了首次赴美使团。他样貌硬朗严肃,又透着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很快吸引了美国媒体的注意。记者们会一窝蜂冲上来将长野围住,叫他“多情汤米”,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年轻女性为他着迷。日报记者关注他的每日行动,密切程度超过了对其上级大使们的关注。长野会在粉色信纸上给美国女孩写情书,这还激发了某个人为长野作波尔卡舞曲一首,重复的副歌部分表达了美国粉丝对长野既爱慕又自我感觉居高临下的古怪热情:
妻子和女仆成群结队
围绕在迷人的小男人身边
人们称他为汤米,机智的汤米,
这个来自日本的,黄种人汤米。
现年28岁的长野,个头没长高,或许也没有了少年时的美丽,但他似乎还自认为是年轻女性的追求对象。然而,跟外国女生调情绝对不同于接触武士的女儿。周围都是美国船员,使节团的领导者们既感到尴尬,又对眼前这一前所未见的情况有些困惑,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审讯;这难道不是文明的西方人会采取的方法吗?这将会是一次对制定使节团对外礼仪有益的审讯,既惩罚了不检点者,又能提供一些乐子。航程漫长,代表们正觉得无聊呢。
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的伊藤在伦敦旅居期间曾观摩过法庭审判,由他来作法官很合适。其他代表中有人作公诉人,有人作辩护律师。佐佐木高行(Takayuki Sasaki)是使节团内掌管司法事务的高级官员,见此场景,他感到很震惊:如果只是用一个虚构的案例来模拟法庭现场,倒不是不可以,可现在面前摆着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这就不一样了。不论这次事件真构成犯罪,还是说只是件有失体统的小事,造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法庭”场子,只会让被骚扰的当事人更难看,也会让整个使节团蒙羞。船还没到岸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外国人会怎么看?
可想而知,这次审判只是一场没有得出任何裁决的闹剧。“一次两次行为失当不会影响西方国家的判断,”愤怒的佐佐木在日记中写道,“但是我们才刚刚走上这条进步之路,我们还是没有学识、没有任何成就的孩子。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做任何错误的决策。”而长野对这次事件则表示不以为然。“这只是为了解闷儿,”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一件小事弄的一个假审判。”这些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记录过亮子在这次事件中所遭受的羞辱,以及其他女孩感到的不适。
亚美利加号乘风破浪,一路向旧金山挺进。大海上的景色平淡无奇,偶尔能看到乘着海风、风筝一样翱翔的信天翁。水手们叫这些信天翁“Goonies”。距到达港口还有两天时,海鸥出现了,它们从乘客的头顶嗖地擦过,飞得是如此之低。“在大海上,”久米写道,“显然,如果你看到信天翁,说明你距离陆地还很远,但如果你看到了海鸥,那么你离陆地就不远了。”此次使团之旅在海上的第一程,终于要结束了。
被家人送走的女孩们,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被使节团的代表们忽略着,她们也没法与美国监护人交流,只能待在自己小小的船舱里,无事可做,脑海里充满了好奇。
前言/序言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女孩。她们出生在自己的国家,却被幼年时代尚无法理解的外力带到一个与家乡全然不同的地方。她们在那里长大,像所有孩子一样,从生活中汲取经验。论出身,她们都纯然是武士的女儿;论成长,她们却是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十年之后,回到故乡的她们发现,在离开的岁月里,她们逐渐长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我和我的父母以及祖父母、曾祖父母都出生在目前居住的这座城市。我本人的经历与我所要讲述的这段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大学的第一天,我遇到一个出生于日本的男孩。年幼时,他的家庭从东京移居西雅图。他的父母决定,等他长到16岁,他们就“回家”。对他而言,他的家就在美国,所以后来他的家人回到了东京,而他却留下来了。
毕业两年,也就是结婚两个月后,我们搬去了东京。从很多方面上看,我在日本的旅居生活都比我丈夫容易得多。随着我的日语不断提高,很多人都夸赞我的口音、举止,以及我在海胆、刺身和腌梅子上的好品位。我的长相使自己在遭遇失败时得到原谅——毕竟我是个外国人。但我丈夫就没有这样的豁免权了。他看起来是日本人,听口音也是日本人——为什么行为举止就不像日本人呢?
三年后,我们回到纽约。我重返校园,攻读东亚文化研究生课程,这时,我迷上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历史。明治时代是生活在天神土地上的日本,开始反思历史、向西方工业文明新偶像学习的时代。一天,在纽约社会图书馆地下室珍贵的藏书中,我发现了一本绿皮书——《窥见日本》(A Japanese Interior)作者是爱丽丝·梅布尔·培根(Alice Mabel Bacon),一位康涅狄格的学校教师。这是本回忆录,培根记录了她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东京与“早就在美国相识多年且关系非常亲密的日本朋友们”一起生活的一年。这太奇怪了。19世纪的美国女性一般不会有日本朋友,更别说是她们在美国认识的日本朋友了。
爱丽丝来自纽黑文市,我正好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大学岁月;她旅居东京的时候并没有和外国人一起住,而是住在日本家庭里,我也一样;她曾在一所日本女校教书,这所学校与100年后我在纽约就读的学校同年建立。她的文字耿直而风趣,让我想起我的老师,她们都是有才情、不做作的女学者,*不喜欢自负之人。从爱丽丝的故事中,我发现了另一位女士——与她的生命有诸多交集的山川舍松,爱丽丝的养妹,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津田梅子,她在日本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语学校,舍松和爱丽丝也参与其中;瓜生永井繁子,早在尚无“全职妈妈”一词的几代人之前,就能在对付七个孩子的同时兼顾一份教师职业了。
我非常认同这些女性。我了解那种感觉——来到日本,没有一点语言基础,努力想要融入日本家庭,同时又对女性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深感不满。我的公公婆婆从未打算培养一个美式思维的孩子,而我丈夫却从来没有以日本人的视角看世界。一百年前,早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每一家公司、每一所学校的目标之前,三个日本女孩跨海跨洲,同时精通两个世界的语言,成为惺惺相惜的挚友。她们的故事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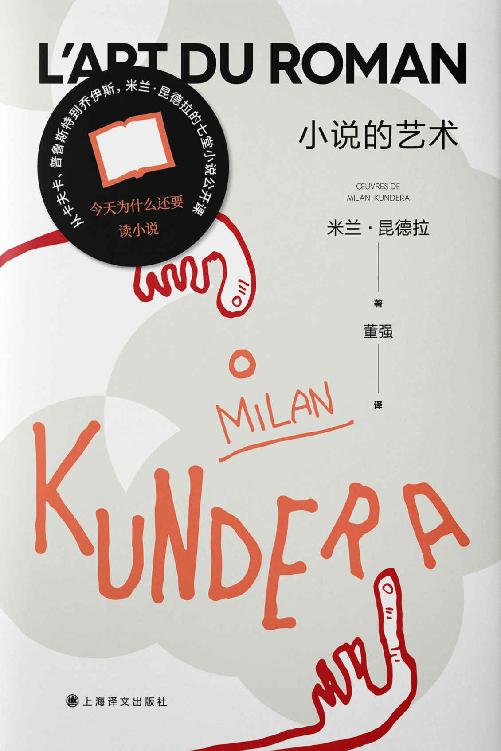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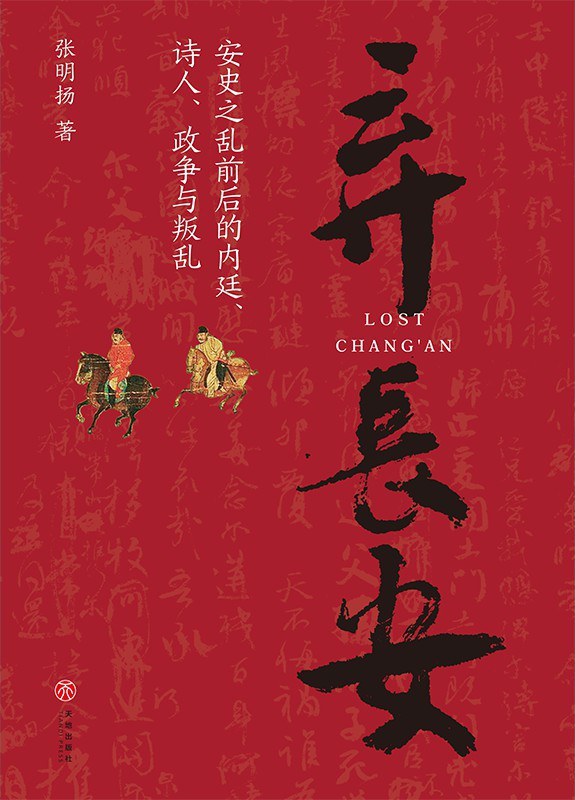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