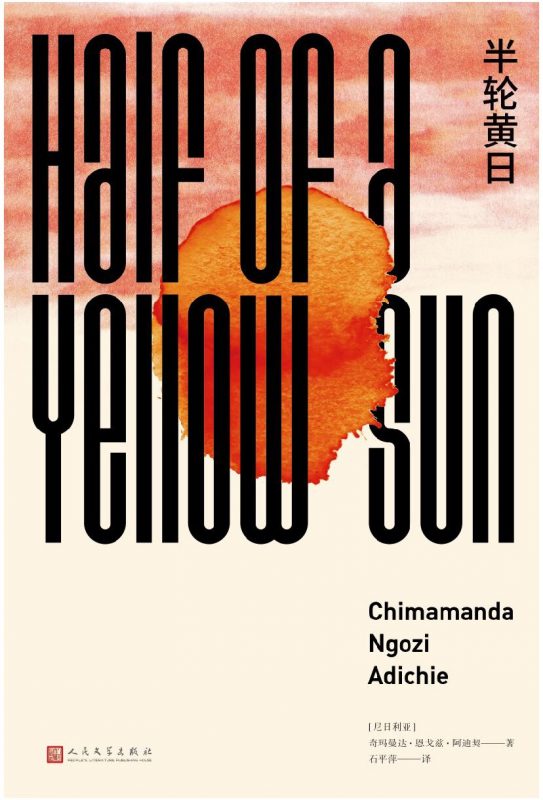
《半轮黄日》是尼日利亚女作家阿迪契为20世纪60年代的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谱写的一曲哀歌。小说以史诗般的结构,通过几对普通男女在尼日利亚内战中经历的变迁,去拷问在荒诞残暴的战争面前,身份、国界、爱情、友谊这些坚固的概念如何幸存……
13岁的乌古家境贫寒,去恩苏卡大学的教授奥登尼博家担任男仆,主人给予他的学习机会让他逐渐摆脱了蒙昧和迷信;伊博族的酋长千金奥兰娜是奥登尼博的女朋友,她的家族在内战前有显赫的声势财富,崇尚自由的奥兰娜却一直与势利投机的家人保持距离;奥兰娜的孪生姐姐凯内内一直照料着家族的生意,她和旅居尼日利亚的英国记者理查德之间产生了爱情,对后殖民主义的虚伪深恶痛绝的理查德一直试图公正客观地记录这个国家经历的一切。
当那场极端残暴的战争爆发,当尼日利亚的北部和南部为后殖民主义的诅咒所驱使并走向自相残杀的结局,这几个主人公的命运随之遽然改变,他们对自我、友谊和爱情的忠诚也面临严峻考验……
编辑推荐
入选BBC评选的“21世纪*伟大的12部小说”
麦克阿瑟天才奖、英联邦作家奖、橘子奖得主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献给尼日利亚的一首挽歌
当爱情、友谊、人性,都和祖国的国界线一样生死攸关…
麦克阿瑟天才奖、英联邦作家奖、橘子奖得主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献给尼日利亚的一首挽歌
当爱情、友谊、人性,都和祖国的国界线一样生死攸关…
作者简介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古,起初在尼日利亚大学学习医药学,后在美国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学习传媒学和政治学,之后在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创意写作的文学硕士学位。
2003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紫木槿》获得2004年橘子小说奖的提名,该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尼日利亚的政治骚乱和一个被信仰裹挟的家庭的悲剧,zui终获得2005年英联邦图书奖*佳新人小说奖。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窥探了尼日利亚的内战伤痛,小说获2007年橘子小说奖。2009年,她的小说《绕颈之物》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提名。
2010年,阿迪契入选《纽约客》评出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2015年,《时代》杂志评选阿迪契为“世界zui有影响力的一百人”。
2014年,她的TED演讲被集结成同名散文集《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她zui近的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佬》呈现了作者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思考和感受,该书摘得2013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小说奖。
2003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紫木槿》获得2004年橘子小说奖的提名,该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尼日利亚的政治骚乱和一个被信仰裹挟的家庭的悲剧,zui终获得2005年英联邦图书奖*佳新人小说奖。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窥探了尼日利亚的内战伤痛,小说获2007年橘子小说奖。2009年,她的小说《绕颈之物》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提名。
2010年,阿迪契入选《纽约客》评出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2015年,《时代》杂志评选阿迪契为“世界zui有影响力的一百人”。
2014年,她的TED演讲被集结成同名散文集《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她zui近的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佬》呈现了作者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思考和感受,该书摘得2013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小说奖。
精彩书评
忠诚什么时候来自于爱,什么时候又来自共同的不幸抑或共同的遗产?《半轮黄日》通过一对双生姐妹纠缠的关系探索了这一问题。和所有身处后殖民时代的尼日利亚人一样,她们的生活身不由己地彼此牵绊,她们和她们的祖国也必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联邦主义和困难重重的分离主义之间进行抉择。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半轮黄日》是一本惊人的杰作,有着充沛的智慧和对人物深刻细腻的刻画——这本书是继阿契贝的《瓦解》和V.S.奈保尔的《大河湾》之后,又一部极具分量的20世纪的经典之作。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我们一般不用“智慧”这样的词语形容新人,但这位年轻的作家具有古老的讲故事的人身上的那种智慧……阿迪契拥有天纵之才。
——钦努阿·阿契贝
目录
1 第一部 六十年代初
129 第二部 六十年代末
225 第三部 六十年代初
283 第四部 六十年代末
472 作者的话
474 作者参考书目
476 但愿我们永远铭记——代译后记
129 第二部 六十年代末
225 第三部 六十年代初
283 第四部 六十年代末
472 作者的话
474 作者参考书目
476 但愿我们永远铭记——代译后记
精彩书摘
“飞机飞那么低,”一个男孩兴奋地说,“我看见了飞行员!”
主人和奥凯奥马首先走出去,走到了公路上。奥凯奥马只穿了汗衫和长裤,看上去瘦小了很多。奥兰娜依旧抱着宝贝坐在地上,结婚礼服上裹着迷彩衬衫。乌古站起来,朝公路下方走去。他听见恩瓦拉医生对奥兰娜说:“让我来扶你。灰尘会弄脏你的裙子。”
一条街以外的玉米研磨加工点附近,一个院子冒着浓烟。两栋房子倒塌了,满地都是灰尘和碎石,一些人发狂地在乱糟糟的水泥堆中挖掘,嘴里说着:“你听见那哭声了吗?听见了吗?”他们的身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银色尘土,看上去像是眼睛睁开、没有四肢的鬼怪。
“孩子还活着,我听见哭声了,我听见了。”有人说。男人们、女人们都围拢过来,帮忙,瞪大眼睛仔细看;一些人也在碎石中挖掘,另一些人旁观,还有一些人尖叫着,打着响指。一辆车正在燃烧;一个女子的尸体倒在边上,衣服全被烧光了,烧黑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粉红的斑斑点点,有人用一个撕坏的黄麻袋盖住了这具尸体,但乌古仍能看见那双僵硬的、漆黑如木炭的腿。天空乌云密布。即将到来的降雨带来了一股潮湿的味道,与烟火燃烧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奥凯奥马和主人一起在碎石堆中挖掘。“我听见了孩子的声音,”又有人说,“我听见了孩子的声音。”
乌古转身离开。地上有一只样式时髦的凉鞋,乌古捡起凉鞋,看了看真皮的绑带和厚实的楔形鞋跟,又放回原处。他想象着穿这只鞋的时尚的年轻女子,为了跑到安全的地方,甩掉了这只鞋。他想知道另一只鞋在哪里。
主人回家后,乌古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背靠着墙。奥兰娜正在拨弄着碟子里的一块蛋糕。她仍旧穿着结婚礼服;奥凯奥马的军装衬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椅子上。客人们都慢慢地离开了,他们几乎没说话,面容暗淡,布满歉疚,仿佛是他们允许空袭破坏了婚礼,因而异常不安。
主人给自己倒了一杯棕榈酒。“你听到那条新闻了吗?”
“没有。”奥兰娜回答。
“我们的军队在中西部占领的地盘全丢了,向拉各斯进军的行动也完蛋了。尼日利亚现在说这是战争,不再是一场警察行动。”他摇摇头。“我们被出卖了。”
“你想吃蛋糕吗?”奥兰娜问。蛋糕摆在中央的桌子上,除了她切掉的那一小块,基本完整。
“现在不吃。”主人喝下棕榈酒,又倒了一杯。“我们要修一个地堡,防止再次发生空袭。”他的语气正常、冷静,仿佛空袭是仁慈的行径,仿佛刚才近在咫尺的不是死亡。他转身对乌古说:“你知道什么是地堡吗,我的好伙计?”
“知道,先生,”乌古回答,“就像希特勒的那个。”“嗯,对,我想差不多。”
“但是,先生,有人说地堡是集体坟墓,”乌古说。
“绝对的胡说八道。地堡比趴在木薯地里安全。”
屋外,黑夜已经来临,偶尔一次闪电,照亮了天空。奥兰娜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尖叫:“宝贝在哪里?宝贝在哪里?”说完撒腿向卧室跑去。
“我的爱,”主人跟在她身后。
“你没听见吗?你没听见他们又来轰炸我们了?”
“是打雷。”主人从背后揽住奥兰娜,抱紧她。“只是打雷。被我们的雨师挡回去的雷雨终于自由了。只是打雷。”
主人抱着奥兰娜,持续了一会儿,奥兰娜终于坐下来,又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
4.书:《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
他辩称,尼日利亚在独立前没有经济。殖民政府实行专制,一种表面仁慈实则残忍、以惠泽英国为主旨的独裁统治。1960年的经济构成是潜能:原材料、人力资源、高昂的士气,以及英
国人拿去重建战后经济剩下的经销管理局的储备金的一部分。还有新近发现的石油。但尼日利亚的新任领导人过于乐观,在推行行将赢得人民信任的发展项目上过于雄心勃勃,在接受剥削性的国外贷款方面过于天真,在盲目模仿英国,又过分热衷于全盘接收尼日利亚人长期以来无从拥有的傲慢态度、更好的医院和更高的工资。他勾勒出这个新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但重点讲述1966年的大屠杀。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伊博族政变”的报复,抗议行将导致北部人在政府文职机构中失利的《中央集权法令》——并不重要。死亡人数的不同统计数字——三千、一万、五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屠杀令伊博族感到恐惧,加强了他们的团结。重要的是,大屠杀使得之前的尼日利亚人变成了热忱的比亚法拉人。
……
主人和奥凯奥马首先走出去,走到了公路上。奥凯奥马只穿了汗衫和长裤,看上去瘦小了很多。奥兰娜依旧抱着宝贝坐在地上,结婚礼服上裹着迷彩衬衫。乌古站起来,朝公路下方走去。他听见恩瓦拉医生对奥兰娜说:“让我来扶你。灰尘会弄脏你的裙子。”
一条街以外的玉米研磨加工点附近,一个院子冒着浓烟。两栋房子倒塌了,满地都是灰尘和碎石,一些人发狂地在乱糟糟的水泥堆中挖掘,嘴里说着:“你听见那哭声了吗?听见了吗?”他们的身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银色尘土,看上去像是眼睛睁开、没有四肢的鬼怪。
“孩子还活着,我听见哭声了,我听见了。”有人说。男人们、女人们都围拢过来,帮忙,瞪大眼睛仔细看;一些人也在碎石中挖掘,另一些人旁观,还有一些人尖叫着,打着响指。一辆车正在燃烧;一个女子的尸体倒在边上,衣服全被烧光了,烧黑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粉红的斑斑点点,有人用一个撕坏的黄麻袋盖住了这具尸体,但乌古仍能看见那双僵硬的、漆黑如木炭的腿。天空乌云密布。即将到来的降雨带来了一股潮湿的味道,与烟火燃烧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奥凯奥马和主人一起在碎石堆中挖掘。“我听见了孩子的声音,”又有人说,“我听见了孩子的声音。”
乌古转身离开。地上有一只样式时髦的凉鞋,乌古捡起凉鞋,看了看真皮的绑带和厚实的楔形鞋跟,又放回原处。他想象着穿这只鞋的时尚的年轻女子,为了跑到安全的地方,甩掉了这只鞋。他想知道另一只鞋在哪里。
主人回家后,乌古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背靠着墙。奥兰娜正在拨弄着碟子里的一块蛋糕。她仍旧穿着结婚礼服;奥凯奥马的军装衬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椅子上。客人们都慢慢地离开了,他们几乎没说话,面容暗淡,布满歉疚,仿佛是他们允许空袭破坏了婚礼,因而异常不安。
主人给自己倒了一杯棕榈酒。“你听到那条新闻了吗?”
“没有。”奥兰娜回答。
“我们的军队在中西部占领的地盘全丢了,向拉各斯进军的行动也完蛋了。尼日利亚现在说这是战争,不再是一场警察行动。”他摇摇头。“我们被出卖了。”
“你想吃蛋糕吗?”奥兰娜问。蛋糕摆在中央的桌子上,除了她切掉的那一小块,基本完整。
“现在不吃。”主人喝下棕榈酒,又倒了一杯。“我们要修一个地堡,防止再次发生空袭。”他的语气正常、冷静,仿佛空袭是仁慈的行径,仿佛刚才近在咫尺的不是死亡。他转身对乌古说:“你知道什么是地堡吗,我的好伙计?”
“知道,先生,”乌古回答,“就像希特勒的那个。”“嗯,对,我想差不多。”
“但是,先生,有人说地堡是集体坟墓,”乌古说。
“绝对的胡说八道。地堡比趴在木薯地里安全。”
屋外,黑夜已经来临,偶尔一次闪电,照亮了天空。奥兰娜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尖叫:“宝贝在哪里?宝贝在哪里?”说完撒腿向卧室跑去。
“我的爱,”主人跟在她身后。
“你没听见吗?你没听见他们又来轰炸我们了?”
“是打雷。”主人从背后揽住奥兰娜,抱紧她。“只是打雷。被我们的雨师挡回去的雷雨终于自由了。只是打雷。”
主人抱着奥兰娜,持续了一会儿,奥兰娜终于坐下来,又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
4.书:《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
他辩称,尼日利亚在独立前没有经济。殖民政府实行专制,一种表面仁慈实则残忍、以惠泽英国为主旨的独裁统治。1960年的经济构成是潜能:原材料、人力资源、高昂的士气,以及英
国人拿去重建战后经济剩下的经销管理局的储备金的一部分。还有新近发现的石油。但尼日利亚的新任领导人过于乐观,在推行行将赢得人民信任的发展项目上过于雄心勃勃,在接受剥削性的国外贷款方面过于天真,在盲目模仿英国,又过分热衷于全盘接收尼日利亚人长期以来无从拥有的傲慢态度、更好的医院和更高的工资。他勾勒出这个新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但重点讲述1966年的大屠杀。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伊博族政变”的报复,抗议行将导致北部人在政府文职机构中失利的《中央集权法令》——并不重要。死亡人数的不同统计数字——三千、一万、五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屠杀令伊博族感到恐惧,加强了他们的团结。重要的是,大屠杀使得之前的尼日利亚人变成了热忱的比亚法拉人。
……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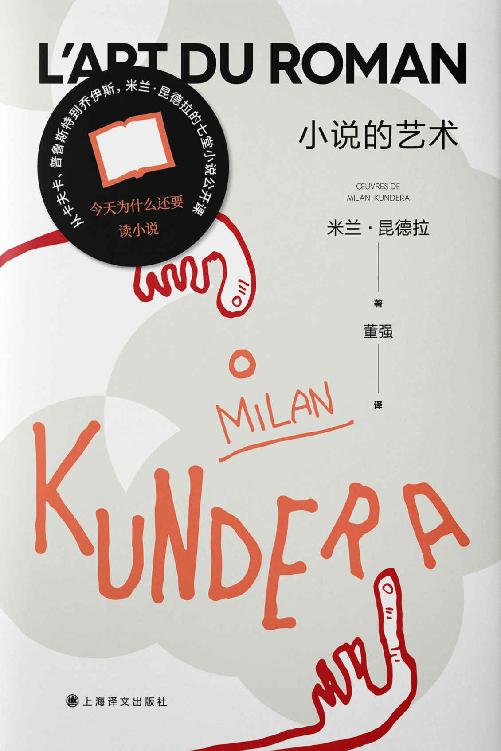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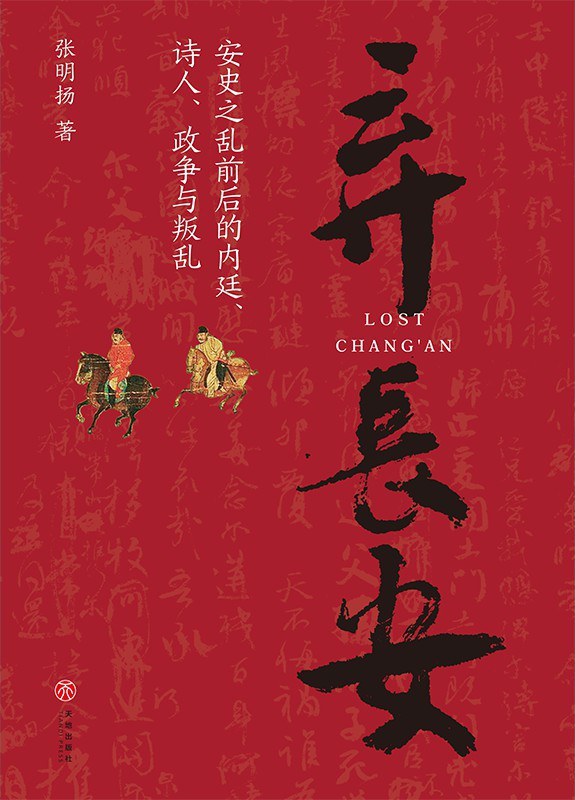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