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x800.jpg?imageMogr2/thumbnail/!1200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200x1600)
本书缘起于作者经家乡塔鱼浜拆迁后,由一只旧碗开始回忆童年的故乡。从“一只供碗”引入,后分为七卷,每卷主题鲜明,进行“关键词回忆和写作”,以物为题展开写江南乡村人的生活,七卷分别为:“地理志”——以单个地点,如“西弄堂”“水泥白场”展开;“地理志附:父亲的老屋”——以老屋各处,如“厢屋”“灶头间”展开;“岁时记”——以各种节日展开;“动物记”——以动物,如“母牛”“狗”等展开;“昆虫记”——以亲近的昆虫,如“蜻蜓”“萤火虫”等展开“农事诗”——以作物的播种、收割、收购的生命历程展开;“草木列传:农事诗补遗”分写了各种童年时期亲近的各种草木。作者“为物立传”,将童年生活的细枝末节作为线索聚集起来,写故乡“自然中人”的日常生活:地点、虫兽、节日、草木……众多的回忆片段汇聚成记忆的河流,还原了江南乡村的肌理,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江南水乡生活的全景图。是一部“文学的自然地方志”,一本“诗意的江南风物回忆录”
编辑推荐
★《东京梦华录》《洛阳伽蓝记》式的记录,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江南水乡生活全景图,描绘乡村生活的肌理。
★地点、虫兽、节日、草木……一部记录20世纪江南乡村的一草一木,岁时流转的“自然史”。
★文学的自然地方志,诗意的江南风物回忆录。
★逝去又永存的故乡:“此时,远非塔鱼浜时光的尽头,而是另一种时间的开始,在云朵崩断的天象之下,塔鱼浜的泥土以及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汉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此塔鱼浜藏身在过往细节的名词和动词中——但我要说它仍是及物的。从此塔鱼浜的少年在有限的疆土里做着无限的漫游——但我必须说,这种漫游的脚尖固执地指向未来。”
★邹汉明走进了南方的腹地,走进了人迹罕至的乡野之地,走进了寻常庭院,走进了一棵树的年轮,并将沿着一片树叶的茎脉,一直走进自己的掌纹:他把自身的微命揉入了整个南方乡村远为繁杂的历史与命运之中。——东君
★地点、虫兽、节日、草木……一部记录20世纪江南乡村的一草一木,岁时流转的“自然史”。
★文学的自然地方志,诗意的江南风物回忆录。
★逝去又永存的故乡:“此时,远非塔鱼浜时光的尽头,而是另一种时间的开始,在云朵崩断的天象之下,塔鱼浜的泥土以及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汉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此塔鱼浜藏身在过往细节的名词和动词中——但我要说它仍是及物的。从此塔鱼浜的少年在有限的疆土里做着无限的漫游——但我必须说,这种漫游的脚尖固执地指向未来。”
★邹汉明走进了南方的腹地,走进了人迹罕至的乡野之地,走进了寻常庭院,走进了一棵树的年轮,并将沿着一片树叶的茎脉,一直走进自己的掌纹:他把自身的微命揉入了整个南方乡村远为繁杂的历史与命运之中。——东君
目录
塔鱼浜地图
引言 一只还魂的供碗
卷一 地理志
塔鱼浜
木桥头
西弄堂
水泥白场
东弄堂
高稻地
机埠
墙内坟
姚亩田渠道口
八分埂
邱家门对
戤壁路
小猪房
六亩头
荡田里
蟹洞田
长坂里
老人下
活杀埂
大水坝
小圩
小水坝
圣堂湾
棉花埂
河的南面
后头田
严家浜
卷二 地理志附 父亲的老屋
草棚,或拦头屋
厢屋
灶头间
房间里
后门头
卷三 岁时记
正月初一
正月初二
正月半
二月初二
三月三
清明
头忙日
立夏日
五月初五
六月六
七夕
七月半
七月三十
八月十五
国庆节
九月九
冬至
十二月廿三
十二月廿四
年节边
十二月廿九
十二月三十
卷四 动物记
母牛
公牛
湖羊
狗
母猪
肉猪
野猫和家猫
公鸡
母鸡故事
母鸡续
兔子
鸭与鹅
卷五 昆虫记
蜘蛛
苍蝇
蚊子
乌蠓
蚤虱
蛆虫
壁虎
蜒蚰
洋夹
胡蜂
胡虻
蜜蜂
蝴蝶
蜻蜓
螳螂
蚂蚁
曲蟮
地鳖虫
洞里毛
金眼乌子
老蝉泥
浮子蝶
刺毛虫
瓦刺虫
角蜢
百脚
男儿虫
寸板虫
萤火虫
赚绩
瓢虫
小青虫
蜗牛
米虫
纺绩娘
蚕
卷六 农事诗
水稻简史
菊花简史
烟叶简史
卷七 农事诗补遗 草木列传
树部
草部
蔬部、豆部、瓜部
后记
引言 一只还魂的供碗
卷一 地理志
塔鱼浜
木桥头
西弄堂
水泥白场
东弄堂
高稻地
机埠
墙内坟
姚亩田渠道口
八分埂
邱家门对
戤壁路
小猪房
六亩头
荡田里
蟹洞田
长坂里
老人下
活杀埂
大水坝
小圩
小水坝
圣堂湾
棉花埂
河的南面
后头田
严家浜
卷二 地理志附 父亲的老屋
草棚,或拦头屋
厢屋
灶头间
房间里
后门头
卷三 岁时记
正月初一
正月初二
正月半
二月初二
三月三
清明
头忙日
立夏日
五月初五
六月六
七夕
七月半
七月三十
八月十五
国庆节
九月九
冬至
十二月廿三
十二月廿四
年节边
十二月廿九
十二月三十
卷四 动物记
母牛
公牛
湖羊
狗
母猪
肉猪
野猫和家猫
公鸡
母鸡故事
母鸡续
兔子
鸭与鹅
卷五 昆虫记
蜘蛛
苍蝇
蚊子
乌蠓
蚤虱
蛆虫
壁虎
蜒蚰
洋夹
胡蜂
胡虻
蜜蜂
蝴蝶
蜻蜓
螳螂
蚂蚁
曲蟮
地鳖虫
洞里毛
金眼乌子
老蝉泥
浮子蝶
刺毛虫
瓦刺虫
角蜢
百脚
男儿虫
寸板虫
萤火虫
赚绩
瓢虫
小青虫
蜗牛
米虫
纺绩娘
蚕
卷六 农事诗
水稻简史
菊花简史
烟叶简史
卷七 农事诗补遗 草木列传
树部
草部
蔬部、豆部、瓜部
后记
前言
20世纪最后那几年,凋敝的塔鱼浜,一户紧挨一户,仍排列在沿河一线。一些带着已逝年代典型印记的两层砖混结构的楼屋(楼建在房子最前头),依然张开巨口,吞吐着农家安静的生活。这个年代的塔鱼浜,粗鄙,单一,样子其实不那么好看,但就是这样一个渐次沦陷于新时光的老村坊,也将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冬天的塔鱼浜向来静落落的,悠闲,自由,静美,有一种太古的气息,屋顶的白云可以逗留大半天而不移步,万物在自身的枯黄里等待着更换容颜。此时,塔鱼浜并不知道,这是它存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冬天。
通往塔鱼浜的乡路迂回曲折,触目尽是灰白的乡土,顿然觉出,我家乡的乡音也有这种淳朴的土白色。小路旁,陈年木槿的枝梢轻擦着白色的车身,屑粒嗦落[1],这在我听来,也很亲切。老邻居们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面朝沃土背朝天,他们依旧在田间地头翻翻垦垦,做着一辈子都做不完的农活。看到我前来,还举着小相机到处乱拍,表示很不理解,好在他们对我总归客气,一些老人停下手头的农活,直起腰来,擦一把汗,开始用塔鱼浜土白喊我的小名,开始问我这种地方有什么可拍的。
确实没什么好拍的。对于村庄的拆迁,说白了,他们并不关心,因为地处僻壤,土地无高价可抬。还有(或者更主要的原因),本村除了极少几个闯荡在外、有经济头脑的家伙外,大多数人木知木觉,远不如城镇近郊农民经济意识强烈。以我常年的观感,塔鱼浜人对经济的盘算,只在乎自家老屋的几个平方不要少算或错算,其他一律马虎不论。概言之,他们听凭村民委派人来丈量,记录,最后定个价,他们签字,表示同意,这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也就完事大吉。在他们看来,拆迁无非履行一道手续,房屋之外的其他补偿,没有去想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谈。比如我家老屋前,父亲种有大片苗木,都长到铁耙柄那么粗了,他也不会想到苗木可以作价补偿。上头尽管眼睛雪亮,但也只当不知道,任凭推土机轰轰隆隆推平了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塔鱼浜老农们都像我父亲一样,对于能够搬去翔厚或炉头,都挺高兴。很多人早就在迎候着推土机的到来。他们觉得新居地离城镇近,或就在炉头镇上,生活就会更加便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此可以做个街上人。街上人的身份,是他们一生的梦想。要知道,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改开”以来,塔鱼浜这样的老村坊,虽说通有简易的乡村公路,但仍属于桐乡最偏僻的深乡下。
很清楚,塔鱼浜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根本挣扎不了多长时间。无论从补偿的传闻、贴出的告示甚或村庄本身的窳败等等,一切都在表明,它将很快走到尽头。
老村坊在随后出台的一种叫作“两分两换”的政策里灰飞烟灭。那天,我记得我的大弟汉良在电话那头略带埋怨的声音:“阿哥,你再不来,塔鱼浜就拆光了。”其时,大型推土机已经进驻,曾经炊烟袅袅的歌哭生聚之地,一下子笼罩在一片灰尘的蘑菇云中。据说塔鱼浜的拆毁只用了半天时间。
一位拍照的朋友开车再一次带我去。经桐乡、皂林、炉头,一路往西,由翔厚入北,车子开在机耕路改筑而成的水泥路上,过东漾潭,我们在许家汇村口折西,来到早先塔鱼浜最东边的高稻地。此时,只留了高稻地三间旧房,其余统统拆除。推土机不给我留一点余地,所到之处,无非大咧咧的一堆废墟。整个塔鱼浜的废墟,沿着一条弯曲的小河堆成一条高耸而冗长的小冈。我爬上这个很有规模的“山冈”,纵目四望,触目惊心,眼前全是折断的五孔板,弯曲的钢筋:筷子那么粗,露出漆黑的一截截……以及断砖和断砖,碎瓦和碎瓦,水泥块和水泥块,一段段依旧板结的墙壁,墙壁上悬挂老物件的铁钉还牢牢钉着,甚至铁钉上的一个蒸架还贴墙好端端地挂着。一些人家丢弃的破旧家具也夹杂其中。所有的木头房架全部散架。这会儿看去,塔鱼浜就是一具扑倒在地的死尸。塔鱼浜打散后,原来,样子一点都不好看,白一块,黑一块,灰一块,要不就是铁锈红(九五砖的颜色)的一大块。倒塌的塔鱼浜,如同刚刚被掐断了呼吸,全然是垂死的颜色。废墟的周边,我依稀认出是一块田、一垄地。我还叫得出其中的田埂和圩塘的名称。村坊不远处的机埠,也还能够辨认。伍启桥流来的小河,流经塔鱼浜的两只大漾潭,黑乎乎的,所幸还在。这三个点,构成了我辨认故土方位的地标。我忽然觉得,塔鱼浜拆除,腾出了空间,天地顿然阔大了。前面,就是村庄曾经的中心木桥头,木桥早就改成水泥桥,但大家还是习惯叫它木桥头。原来,木桥是那么小而不起眼。小河南边,几株高大的楝树和香樟树孤零零地站着,好似在低头默哀,旁边一大片低矮的桑树,抱头蹙眉,附和着刚刚降临的死一般的寂静。
我显然迟到了一步,就这一步,塔鱼浜已经拆得干干净净。我没有见到它最后倒下的那个瞬间。我赶到时,龅牙的老炳其站在自家厢屋的废墟上发呆。他木然,惘然,像是自语,又似在告诉我:“没了,押光掀天(全部)……一点都没了。房子拆掉的时候,西边的掌宝嚎啕大哭。”看到推土机的大畚兜起起落落,墙摧屋倒,轰隆巨响之际,几个年老的妇女一齐哭出声来。这就对了,应该有人哭出声来,以前,村里每有老辈故去,总有孝子贤孙围着他哭丧。哭泣,是给一个老人送终的最好表达。理所当然,哭泣也是给一个老村送终的最好表达。很遗憾,我没有见到这年头到处拆这拆那的推土机——那股不可一世的蛮力,它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同一时间,塔鱼浜北面的彭家村、金家角,东面的许家汇,全都拆毁了。毫无疑问,推土机是改村换乡的主角,它们忙忙碌碌,到处显摆,也总是吃力不讨好。
冬天的塔鱼浜向来静落落的,悠闲,自由,静美,有一种太古的气息,屋顶的白云可以逗留大半天而不移步,万物在自身的枯黄里等待着更换容颜。此时,塔鱼浜并不知道,这是它存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冬天。
通往塔鱼浜的乡路迂回曲折,触目尽是灰白的乡土,顿然觉出,我家乡的乡音也有这种淳朴的土白色。小路旁,陈年木槿的枝梢轻擦着白色的车身,屑粒嗦落[1],这在我听来,也很亲切。老邻居们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面朝沃土背朝天,他们依旧在田间地头翻翻垦垦,做着一辈子都做不完的农活。看到我前来,还举着小相机到处乱拍,表示很不理解,好在他们对我总归客气,一些老人停下手头的农活,直起腰来,擦一把汗,开始用塔鱼浜土白喊我的小名,开始问我这种地方有什么可拍的。
确实没什么好拍的。对于村庄的拆迁,说白了,他们并不关心,因为地处僻壤,土地无高价可抬。还有(或者更主要的原因),本村除了极少几个闯荡在外、有经济头脑的家伙外,大多数人木知木觉,远不如城镇近郊农民经济意识强烈。以我常年的观感,塔鱼浜人对经济的盘算,只在乎自家老屋的几个平方不要少算或错算,其他一律马虎不论。概言之,他们听凭村民委派人来丈量,记录,最后定个价,他们签字,表示同意,这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也就完事大吉。在他们看来,拆迁无非履行一道手续,房屋之外的其他补偿,没有去想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谈。比如我家老屋前,父亲种有大片苗木,都长到铁耙柄那么粗了,他也不会想到苗木可以作价补偿。上头尽管眼睛雪亮,但也只当不知道,任凭推土机轰轰隆隆推平了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塔鱼浜老农们都像我父亲一样,对于能够搬去翔厚或炉头,都挺高兴。很多人早就在迎候着推土机的到来。他们觉得新居地离城镇近,或就在炉头镇上,生活就会更加便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此可以做个街上人。街上人的身份,是他们一生的梦想。要知道,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改开”以来,塔鱼浜这样的老村坊,虽说通有简易的乡村公路,但仍属于桐乡最偏僻的深乡下。
很清楚,塔鱼浜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根本挣扎不了多长时间。无论从补偿的传闻、贴出的告示甚或村庄本身的窳败等等,一切都在表明,它将很快走到尽头。
老村坊在随后出台的一种叫作“两分两换”的政策里灰飞烟灭。那天,我记得我的大弟汉良在电话那头略带埋怨的声音:“阿哥,你再不来,塔鱼浜就拆光了。”其时,大型推土机已经进驻,曾经炊烟袅袅的歌哭生聚之地,一下子笼罩在一片灰尘的蘑菇云中。据说塔鱼浜的拆毁只用了半天时间。
一位拍照的朋友开车再一次带我去。经桐乡、皂林、炉头,一路往西,由翔厚入北,车子开在机耕路改筑而成的水泥路上,过东漾潭,我们在许家汇村口折西,来到早先塔鱼浜最东边的高稻地。此时,只留了高稻地三间旧房,其余统统拆除。推土机不给我留一点余地,所到之处,无非大咧咧的一堆废墟。整个塔鱼浜的废墟,沿着一条弯曲的小河堆成一条高耸而冗长的小冈。我爬上这个很有规模的“山冈”,纵目四望,触目惊心,眼前全是折断的五孔板,弯曲的钢筋:筷子那么粗,露出漆黑的一截截……以及断砖和断砖,碎瓦和碎瓦,水泥块和水泥块,一段段依旧板结的墙壁,墙壁上悬挂老物件的铁钉还牢牢钉着,甚至铁钉上的一个蒸架还贴墙好端端地挂着。一些人家丢弃的破旧家具也夹杂其中。所有的木头房架全部散架。这会儿看去,塔鱼浜就是一具扑倒在地的死尸。塔鱼浜打散后,原来,样子一点都不好看,白一块,黑一块,灰一块,要不就是铁锈红(九五砖的颜色)的一大块。倒塌的塔鱼浜,如同刚刚被掐断了呼吸,全然是垂死的颜色。废墟的周边,我依稀认出是一块田、一垄地。我还叫得出其中的田埂和圩塘的名称。村坊不远处的机埠,也还能够辨认。伍启桥流来的小河,流经塔鱼浜的两只大漾潭,黑乎乎的,所幸还在。这三个点,构成了我辨认故土方位的地标。我忽然觉得,塔鱼浜拆除,腾出了空间,天地顿然阔大了。前面,就是村庄曾经的中心木桥头,木桥早就改成水泥桥,但大家还是习惯叫它木桥头。原来,木桥是那么小而不起眼。小河南边,几株高大的楝树和香樟树孤零零地站着,好似在低头默哀,旁边一大片低矮的桑树,抱头蹙眉,附和着刚刚降临的死一般的寂静。
我显然迟到了一步,就这一步,塔鱼浜已经拆得干干净净。我没有见到它最后倒下的那个瞬间。我赶到时,龅牙的老炳其站在自家厢屋的废墟上发呆。他木然,惘然,像是自语,又似在告诉我:“没了,押光掀天(全部)……一点都没了。房子拆掉的时候,西边的掌宝嚎啕大哭。”看到推土机的大畚兜起起落落,墙摧屋倒,轰隆巨响之际,几个年老的妇女一齐哭出声来。这就对了,应该有人哭出声来,以前,村里每有老辈故去,总有孝子贤孙围着他哭丧。哭泣,是给一个老人送终的最好表达。理所当然,哭泣也是给一个老村送终的最好表达。很遗憾,我没有见到这年头到处拆这拆那的推土机——那股不可一世的蛮力,它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同一时间,塔鱼浜北面的彭家村、金家角,东面的许家汇,全都拆毁了。毫无疑问,推土机是改村换乡的主角,它们忙忙碌碌,到处显摆,也总是吃力不讨好。
精彩书摘
自然村,在浙江省桐乡县西北二十里许,向属炉镇,或属于任何一处僻静的旧江南。
村庄旧名塔鱼浜。六家姓:邹、施、严、金、周、许。严姓只两家。金姓、周姓、许姓各一家。邹与施,基本持平。邹姓居东、居北,施姓居西。承包到户后,据此又分邹介里、施介里。两“介里”多有来往,亲密依旧,也不分彼此。但外人不大分得清邹介里施介里,因此很少叫口。老辈人出口,还是老地名:塔鱼浜。自然,亲切,又好听。
村庄的面前是一条小河,西边的白马塘转弯抹角通过来的。有了这条小河,塔鱼浜的船只可以上南入北去附近的小镇,去老远、更老远的大城市了。河没有名字,或者,塔鱼浜就是这条小河的名字吧。河也没有镇上的河那样整整齐齐的石帮岸。它的南岸,爬着好多树根,北岸长满矮扁扁的青草。河南是成片的桑树地,再过去就是一种风来,稻浪壮阔的水稻田;河之北与人家的白场相连,这白场,塔鱼浜人叫稻地,即盛夏晒稻谷的晒场。稻地前,临河一线有几棵沧桑的枣树,树皮灰白,粗糙,有一种刀砍不入的顽固的面相。每年七八月间,台风像年节,准时穿越广阔的稻田,准点到达塔鱼浜。而稻地外瘦高的枣树,也一定会啪嗒啪嗒掉好一阵子的青大枣。
塔鱼浜的枣树以邹金龙家的最高耸。每年,枣子坐果其实并不多。台风季节,这茧子大小的果实(形状也像茧),淡黄中已有紫色的斑痕,硬邦邦的,挂在枝头,人从下面走过,徒有艳羡的份。通常,四五个顽皮的小毛孩,捡起地上的碎瓦片,一二三,绷紧的身子里发一声喊,嗖嗖嗖,一齐向枣树枝头掷去。未及两三颗枣子落地,辣钵金龙的小脚母亲,后脑勺顶一个拳头大的发髻,拄一根油腻腻的龙头拐杖,张着已没剩几颗牙的一张瘪嘴,凶神恶煞一般,紧趋着小步,追骂出矮闼门来了。老婆子还作势举一举那根永不离手、骇人倒怪的黑漆拐杖,嘴角边露出一颗弯钩似的黄牙。这边,胆子小的,逃还都来不及呢。
每隔三四户,空白的稻地外就有一个河埠头,俗呼桥洞(据音)。整齐的石级一级连着一级通向河水,邻家的农妇来此或淘米洗菜,或洗手洗衣服,间或照看一下自己那张有时清晰有时又模糊的面影,小拇指翘起,勾一下披散的头发。此地离白马塘(外河)三里许,河面上,难得有船只往来,河埠头的河水极少有大涨大落的机会。我家乡塔鱼浜的水,因此是一贯的碧清见底。
在辣钵金龙家的河埠头,七岁那年,我学会了游泳。我抱着一根大门闩,莽撞地跳进河中央。我游了几次,扔下那段壮实的木头,开始了从此岸扑向彼岸的游水。正扑腾得高兴,同村的跷脚(跛足)建林一个浪头打过来,我连吃几口冷水,身子忽然不听使唤,开始下沉。我半沉在河里,但见河边看游水的男男女女,一个个在无声地微笑——那些微笑,还有河边房子那些高高的瓦楞沟,竟是那么冷漠和遥远,而且世间凡我所能看到的事物,都渐渐地在变形,在远去。我在水中,嗓子被堵住,一时三刻喊不出救命的声音。好在比我大几岁的一位叫金美的女孩站在河岸上替我喊了出来。跷脚回身一看,顿觉大事不好,立即游到我身旁,一伸手,拉我到了岸边——这是我第一次和神秘的死神面对面地打了一次小交道。
塔鱼浜西边两里路外的白马塘,是一条大河,也是南北交通的黄金水道。北横头直通乌镇,南横头折西一点就是石门镇,两个老镇好像被白马塘这根长扁担一肩挑着。每天两个班次的轮船途经白马塘伍启桥,三里路开外的塔鱼浜,河埠头的水就会微微上涨:先是河两岸的水草缓缓挨近两岸,接着,水又缓缓地往河中央回落,河里方方正正的一大块水草,一般总有草绳系在岸边的木桩上,这时候,绷紧的草绳“叭”的一声就断了。好在断了绳的水草也不会漂移到别处。过一会儿,毛毯似的水草,还是老样子,仍旧懒洋洋地待在塔鱼浜的水里。
村庄旧名塔鱼浜。六家姓:邹、施、严、金、周、许。严姓只两家。金姓、周姓、许姓各一家。邹与施,基本持平。邹姓居东、居北,施姓居西。承包到户后,据此又分邹介里、施介里。两“介里”多有来往,亲密依旧,也不分彼此。但外人不大分得清邹介里施介里,因此很少叫口。老辈人出口,还是老地名:塔鱼浜。自然,亲切,又好听。
村庄的面前是一条小河,西边的白马塘转弯抹角通过来的。有了这条小河,塔鱼浜的船只可以上南入北去附近的小镇,去老远、更老远的大城市了。河没有名字,或者,塔鱼浜就是这条小河的名字吧。河也没有镇上的河那样整整齐齐的石帮岸。它的南岸,爬着好多树根,北岸长满矮扁扁的青草。河南是成片的桑树地,再过去就是一种风来,稻浪壮阔的水稻田;河之北与人家的白场相连,这白场,塔鱼浜人叫稻地,即盛夏晒稻谷的晒场。稻地前,临河一线有几棵沧桑的枣树,树皮灰白,粗糙,有一种刀砍不入的顽固的面相。每年七八月间,台风像年节,准时穿越广阔的稻田,准点到达塔鱼浜。而稻地外瘦高的枣树,也一定会啪嗒啪嗒掉好一阵子的青大枣。
塔鱼浜的枣树以邹金龙家的最高耸。每年,枣子坐果其实并不多。台风季节,这茧子大小的果实(形状也像茧),淡黄中已有紫色的斑痕,硬邦邦的,挂在枝头,人从下面走过,徒有艳羡的份。通常,四五个顽皮的小毛孩,捡起地上的碎瓦片,一二三,绷紧的身子里发一声喊,嗖嗖嗖,一齐向枣树枝头掷去。未及两三颗枣子落地,辣钵金龙的小脚母亲,后脑勺顶一个拳头大的发髻,拄一根油腻腻的龙头拐杖,张着已没剩几颗牙的一张瘪嘴,凶神恶煞一般,紧趋着小步,追骂出矮闼门来了。老婆子还作势举一举那根永不离手、骇人倒怪的黑漆拐杖,嘴角边露出一颗弯钩似的黄牙。这边,胆子小的,逃还都来不及呢。
每隔三四户,空白的稻地外就有一个河埠头,俗呼桥洞(据音)。整齐的石级一级连着一级通向河水,邻家的农妇来此或淘米洗菜,或洗手洗衣服,间或照看一下自己那张有时清晰有时又模糊的面影,小拇指翘起,勾一下披散的头发。此地离白马塘(外河)三里许,河面上,难得有船只往来,河埠头的河水极少有大涨大落的机会。我家乡塔鱼浜的水,因此是一贯的碧清见底。
在辣钵金龙家的河埠头,七岁那年,我学会了游泳。我抱着一根大门闩,莽撞地跳进河中央。我游了几次,扔下那段壮实的木头,开始了从此岸扑向彼岸的游水。正扑腾得高兴,同村的跷脚(跛足)建林一个浪头打过来,我连吃几口冷水,身子忽然不听使唤,开始下沉。我半沉在河里,但见河边看游水的男男女女,一个个在无声地微笑——那些微笑,还有河边房子那些高高的瓦楞沟,竟是那么冷漠和遥远,而且世间凡我所能看到的事物,都渐渐地在变形,在远去。我在水中,嗓子被堵住,一时三刻喊不出救命的声音。好在比我大几岁的一位叫金美的女孩站在河岸上替我喊了出来。跷脚回身一看,顿觉大事不好,立即游到我身旁,一伸手,拉我到了岸边——这是我第一次和神秘的死神面对面地打了一次小交道。
塔鱼浜西边两里路外的白马塘,是一条大河,也是南北交通的黄金水道。北横头直通乌镇,南横头折西一点就是石门镇,两个老镇好像被白马塘这根长扁担一肩挑着。每天两个班次的轮船途经白马塘伍启桥,三里路开外的塔鱼浜,河埠头的水就会微微上涨:先是河两岸的水草缓缓挨近两岸,接着,水又缓缓地往河中央回落,河里方方正正的一大块水草,一般总有草绳系在岸边的木桩上,这时候,绷紧的草绳“叭”的一声就断了。好在断了绳的水草也不会漂移到别处。过一会儿,毛毯似的水草,还是老样子,仍旧懒洋洋地待在塔鱼浜的水里。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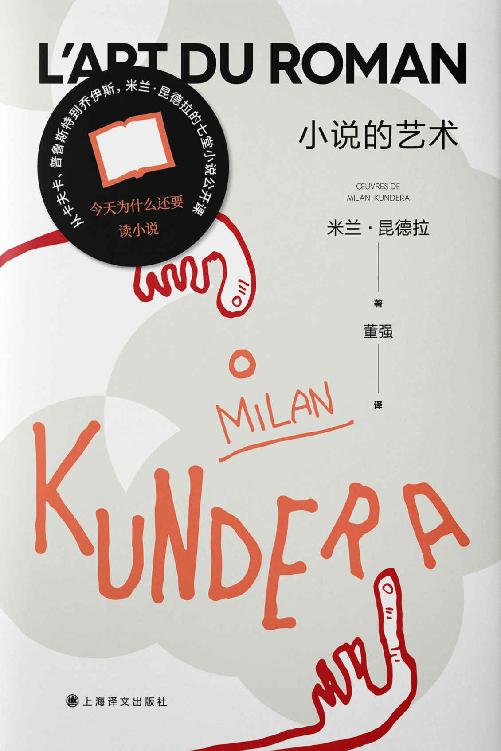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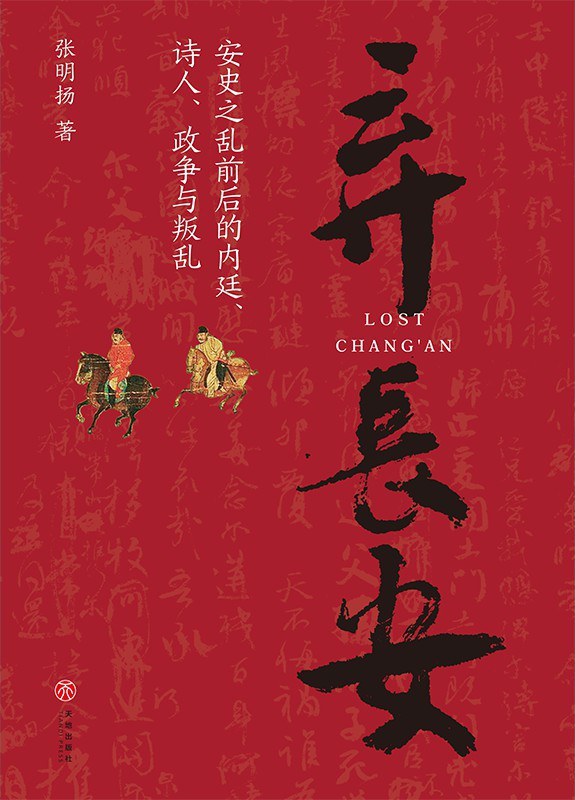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