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只来自墨西哥南部的蝾螈目动物,比一根火柴棒还要小;一种白色的粗尾猴,生活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生长于安第斯山脉的小型犬浣熊,看起来像是猫鼬,又像是泰迪熊。
这些神奇的物种都是新物种,它们的命名是不久前确定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而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柜里和洞穴般的地下室里被发掘出来的。正如本书中揭示的那样,藏在自然博物馆的大量标本是一项有待发现的宝藏。
跟随肯普的引导,我们去博物馆的地下室寻找标本,检查抽屉和藏品罐,探索新物种。这里面有1906年收集的帝王蟹、不明种类的狼蛛、被错误标记的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蜗牛、由达尔文收集的不为人知的甲虫、一种被人忽视的小青蛙,还有其他的神秘物种。
在每一段故事中,这些标本都静静地等待了几十年,有时甚至超过了一个世纪。在敏锐的科学家们意识到它们是新物种之前,它们一直藏于自然博物馆的藏品库里。科学家们每年都会在博物馆的藏品库里发现新的物种。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只命名了生活在世界上的一小部分物种。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标本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才被命名,甚至它们在被命名之前就已经从野外消失了,它们是气候变化和栖息地丧失的受害者。这些故事也告诉我们,标本持久保存的重要性。
《失落的物种》生动地讲述了这些故事——从每一个生物标本的最新信息到收集它们的人,还有那些最终意识到它们是新物种的科学家们——并将激励人们去探索自然博物馆藏品背后更多的故事。
编辑推荐
在自然博物馆的预算日益减少之际,肯普创作的《失落的物种》表明了这些博物馆的藏品在鉴定新物种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管理分类学专业知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认可……肯普巧妙地证明了自然博物馆藏品和具有分类学专业知识的策展人在记录新物种和最终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藏品需要维护,以确保为下一代分类学家保存标本和文件,他们将发现更多的新物种。我希望《失落的物种》能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兴趣,并支持这些努力。”
——邦妮·斯泰尔斯《科学》杂志
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庞大,积压如山,错误百出,分类描述不完整。想想19世纪和20世纪的探险吧。想象一下,自然博物馆的抽屉里有成千上万只甲虫和苍蝇,数不清的罐子里装着海洋无脊椎动物。这些藏品里还有多少珍宝等待着被发现呢?生物学家肯普也对此感到疑惑。他继续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藏品,并在本书中记录了他的发现……一段段神奇的故事。”
——艾拉·弗莱托,《科学星期五》
这是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愉快并且收获颇丰的阅读之旅。本书的每一章都给出一个物种或一个属的简要描述,这些物种或属通常是在博物馆标本收集几十年后才被正式命名的。其中大多数动物在过去15年内被描述和命名的,包括闪电蟑螂、隐身节蛙、来自新几内亚的西巴布亚鼠袋狸、红宝石海龙和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地点捕获的原子狼蛛。”
——《华尔街日报》
当肯普告诉我们这些鼓舞人心的发现时,你会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在自己身边的自然博物馆里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宝藏。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的物种。目前,据估计,地球上有1000万~3000万种物种,其中被命名的只有不到200万种。但令人惊讶的是,博物馆中有多达一半的标本被错误地分类了。很显然,还有许多分类学和系统学的研究要做。《失落的物种》引人入胜,有力地证明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体价值,以及研究这些藏品的重要性。
——GrrlScientist《福布斯》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一部分,克里斯托弗·肯普在本书中生动地讲述了保存下来的标本在基础研究中的价值。通过这些研究,他成功地将科学、历史和探险融合起来。
——“当代达尔文”,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Wilson)
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自然博物馆总共收藏了数十亿件珍贵的科学标本。在这些汇集了几个世纪的生命和文化的宝藏之中,每一件标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克里斯托弗·肯普生动地讲述了其中一些标本的故事,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主角,从卑微的线虫到强大的雷龙。他把这些标本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不仅可以展示地球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作为人类探索发现和最终研究的范例。任何对自然博物馆藏品感兴趣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它说明了这些藏品是如何收集的,以及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什么。
——《策展人》作者兰斯·格兰德(Lance Grande)
自然博物馆中总是充满了惊喜——从飞狐到帝王蟹,它们在标本架上等待被人研究。克里斯托弗·肯普将这些标本以及收集和描述这些标本的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失落的物种》会让所有喜欢发现、探险的故事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也会被那些让关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读者所喜爱。
——《物种探寻者》作者理查德·康尼夫(Richard Conniff)
克里斯托弗·肯普精彩地讲述了自然博物馆藏品不为人知的故事,有很多新物种其实收藏在博物馆的标本抽屉和罐子里。喜欢探险并对博物馆、历史和生物多样性感兴趣的读者能在《失落的物种》中找到大量有趣的故事,这是一种有趣的、迷人的、对话式的阅读。
——《蝾螈之眼和青蛙之趾》作者马蒂·克伦普(Marty Crump)
——邦妮·斯泰尔斯《科学》杂志
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庞大,积压如山,错误百出,分类描述不完整。想想19世纪和20世纪的探险吧。想象一下,自然博物馆的抽屉里有成千上万只甲虫和苍蝇,数不清的罐子里装着海洋无脊椎动物。这些藏品里还有多少珍宝等待着被发现呢?生物学家肯普也对此感到疑惑。他继续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藏品,并在本书中记录了他的发现……一段段神奇的故事。”
——艾拉·弗莱托,《科学星期五》
这是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愉快并且收获颇丰的阅读之旅。本书的每一章都给出一个物种或一个属的简要描述,这些物种或属通常是在博物馆标本收集几十年后才被正式命名的。其中大多数动物在过去15年内被描述和命名的,包括闪电蟑螂、隐身节蛙、来自新几内亚的西巴布亚鼠袋狸、红宝石海龙和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地点捕获的原子狼蛛。”
——《华尔街日报》
当肯普告诉我们这些鼓舞人心的发现时,你会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在自己身边的自然博物馆里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宝藏。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的物种。目前,据估计,地球上有1000万~3000万种物种,其中被命名的只有不到200万种。但令人惊讶的是,博物馆中有多达一半的标本被错误地分类了。很显然,还有许多分类学和系统学的研究要做。《失落的物种》引人入胜,有力地证明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体价值,以及研究这些藏品的重要性。
——GrrlScientist《福布斯》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一部分,克里斯托弗·肯普在本书中生动地讲述了保存下来的标本在基础研究中的价值。通过这些研究,他成功地将科学、历史和探险融合起来。
——“当代达尔文”,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Wilson)
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自然博物馆总共收藏了数十亿件珍贵的科学标本。在这些汇集了几个世纪的生命和文化的宝藏之中,每一件标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克里斯托弗·肯普生动地讲述了其中一些标本的故事,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主角,从卑微的线虫到强大的雷龙。他把这些标本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不仅可以展示地球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作为人类探索发现和最终研究的范例。任何对自然博物馆藏品感兴趣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它说明了这些藏品是如何收集的,以及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什么。
——《策展人》作者兰斯·格兰德(Lance Grande)
自然博物馆中总是充满了惊喜——从飞狐到帝王蟹,它们在标本架上等待被人研究。克里斯托弗·肯普将这些标本以及收集和描述这些标本的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失落的物种》会让所有喜欢发现、探险的故事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也会被那些让关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读者所喜爱。
——《物种探寻者》作者理查德·康尼夫(Richard Conniff)
克里斯托弗·肯普精彩地讲述了自然博物馆藏品不为人知的故事,有很多新物种其实收藏在博物馆的标本抽屉和罐子里。喜欢探险并对博物馆、历史和生物多样性感兴趣的读者能在《失落的物种》中找到大量有趣的故事,这是一种有趣的、迷人的、对话式的阅读。
——《蝾螈之眼和青蛙之趾》作者马蒂·克伦普(Marty Crump)
目录
献给
引言
脊椎动物
高耸入云:小型犬浣熊(Bassaricyon neblina)
在83色码的天空下:乌查岭鼠(Thomasomys ucucha)
捕貘之行:卡波马尼貘(Tapirus kabomani)
分类的困惑:萨基猴(Pithecia genus)
散布世界各地:西巴布亚鼠袋狸(Microperoryctes aplini)
160年后得以命名:华莱士慈鲷(Crenicichla monicae)
这里有龙:红宝石海龙(Phyllopteryx dewysea)
在罐中度过一个世纪:索里螈属(Thorius Salamanders)
出自一口绿坩埚:隐身节蛙(Arthroleptis kutogundua)
身体和断开的尾巴:史密斯隐身壁虎(Cyrtodactylus celatus)
无脊椎动物
顺带获得的珍宝:瘿蜂(Cynipoidea)
拟态生物:闪电蟑螂(Lucihormetica luckae)
潜于虫群之下:达尔文隐翅甲(Darwinilus sedarisi)
遥远战争的战利品:刚果长尾蜓(Gynacantha congolica)
分成两半的标本:缪尔楔形甲虫(Rhipidocyrtus muiri)
玛丽·金斯利天牛(Pseudictator kingsleyae)
巨型苍蝇(Gauromydas papavero和Gauromydas mateus)
来自51区:原子狼蛛(Aphonopelma atomicum)
最周到的主人:螺旋线虫(Ohbayashinema aspeira)
来自克伦威尔路的时光机器:阿布莱特蜗牛(Pseudopomatias abletti)
无尽旷野:倍登等足虫(Exosphaeroma paydenae)
浑身是刺:马卡罗夫帝王蟹(Paralomis makarovi)
植物
宜家袋里:香莓藤属植物(Monanthotaxis Genus)
其他
在石膏里等待:化石——埃尔默·里格斯收集的古生物标本
第一件艺术品:早期人类雕刻——一片有50万年历史的贝壳
后记
引言
脊椎动物
高耸入云:小型犬浣熊(Bassaricyon neblina)
在83色码的天空下:乌查岭鼠(Thomasomys ucucha)
捕貘之行:卡波马尼貘(Tapirus kabomani)
分类的困惑:萨基猴(Pithecia genus)
散布世界各地:西巴布亚鼠袋狸(Microperoryctes aplini)
160年后得以命名:华莱士慈鲷(Crenicichla monicae)
这里有龙:红宝石海龙(Phyllopteryx dewysea)
在罐中度过一个世纪:索里螈属(Thorius Salamanders)
出自一口绿坩埚:隐身节蛙(Arthroleptis kutogundua)
身体和断开的尾巴:史密斯隐身壁虎(Cyrtodactylus celatus)
无脊椎动物
顺带获得的珍宝:瘿蜂(Cynipoidea)
拟态生物:闪电蟑螂(Lucihormetica luckae)
潜于虫群之下:达尔文隐翅甲(Darwinilus sedarisi)
遥远战争的战利品:刚果长尾蜓(Gynacantha congolica)
分成两半的标本:缪尔楔形甲虫(Rhipidocyrtus muiri)
玛丽·金斯利天牛(Pseudictator kingsleyae)
巨型苍蝇(Gauromydas papavero和Gauromydas mateus)
来自51区:原子狼蛛(Aphonopelma atomicum)
最周到的主人:螺旋线虫(Ohbayashinema aspeira)
来自克伦威尔路的时光机器:阿布莱特蜗牛(Pseudopomatias abletti)
无尽旷野:倍登等足虫(Exosphaeroma paydenae)
浑身是刺:马卡罗夫帝王蟹(Paralomis makarovi)
植物
宜家袋里:香莓藤属植物(Monanthotaxis Genus)
其他
在石膏里等待:化石——埃尔默·里格斯收集的古生物标本
第一件艺术品:早期人类雕刻——一片有50万年历史的贝壳
后记
媒体评论
在自然博物馆的预算日益减少之际,肯普创作的《失落的物种》表明了这些博物馆的藏品在鉴定新物种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管理分类学专业知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认可……肯普巧妙地证明了自然博物馆藏品和具有分类学专业知识的策展人在记录新物种和*终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藏品需要维护,以确保为下一代分类学家保存标本和文件,他们将发现更多的新物种。我希望《失落的物种》能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兴趣,并支持这些努力。”
——邦妮·斯泰尔斯《科学》杂志
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庞大,积压如山,错误百出,分类描述不完整。想想19世纪和20世纪的探险吧。想象一下,自然博物馆的抽屉里有成千上万只甲虫和苍蝇,数不清的罐子里装着海洋无脊椎动物。这些藏品里还有多少珍宝等待着被发现呢?生物学家肯普也对此感到疑惑。他继续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藏品,并在本书中记录了他的发现……一段段神奇的故事。”
——艾拉·弗莱托,《科学星期五》
这是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愉快并且收获颇丰的阅读之旅。本书的每一章都给出一个物种或一个属的简要描述,这些物种或属通常是在博物馆标本收集几十年后才被正式命名的。其中大多数动物在过去15年内被描述和命名的,包括闪电蟑螂、隐身节蛙、来自新几内亚的西巴布亚鼠袋狸、红宝石海龙和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地点捕获的原子狼蛛。”
——《华尔街日报》
当肯普告诉我们这些鼓舞人心的发现时,你会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在自己身边的自然博物馆里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宝藏。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的物种。目前,据估计,地球上有1000万~3000万种物种,其中被命名的只有不到200万种。但令人惊讶的是,博物馆中有多达一半的标本被错误地分类了。很显然,还有许多分类学和系统学的研究要做。《失落的物种》引人入胜,有力地证明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体价值,以及研究这些藏品的重要性。
——GrrlScientist《福布斯》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一部分,克里斯托弗·肯普在本书中生动地讲述了保存下来的标本在基础研究中的价值。通过这些研究,他成功地将科学、历史和探险融合起来。
——“当代达尔文”,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Wilson)
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自然博物馆总共收藏了数十亿件珍贵的科学标本。在这些汇集了几个世纪的生命和文化的宝藏之中,每一件标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克里斯托弗·肯普生动地讲述了其中一些标本的故事,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主角,从卑微的线虫到强大的雷龙。他把这些标本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不仅可以展示地球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作为人类探索发现和*终研究的范例。任何对自然博物馆藏品感兴趣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它说明了这些藏品是如何收集的,以及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什么。
——《策展人》作者兰斯·格兰德(Lance Grande)
自然博物馆中总是充满了惊喜——从飞狐到帝王蟹,它们在标本架上等待被人研究。克里斯托弗·肯普将这些标本以及收集和描述这些标本的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失落的物种》会让所有喜欢发现、探险的故事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也会被那些让关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读者所喜爱。
——《物种探寻者》作者理查德·康尼夫(Richard Conniff)
克里斯托弗·肯普精彩地讲述了自然博物馆藏品不为人知的故事,有很多新物种其实收藏在博物馆的标本抽屉和罐子里。喜欢探险并对博物馆、历史和生物多样性感兴趣的读者能在《失落的物种》中找到大量有趣的故事,这是一种有趣的、迷人的、对话式的阅读。
——《蝾螈之眼和青蛙之趾》作者马蒂·克伦普(Marty Crump)
——邦妮·斯泰尔斯《科学》杂志
自然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庞大,积压如山,错误百出,分类描述不完整。想想19世纪和20世纪的探险吧。想象一下,自然博物馆的抽屉里有成千上万只甲虫和苍蝇,数不清的罐子里装着海洋无脊椎动物。这些藏品里还有多少珍宝等待着被发现呢?生物学家肯普也对此感到疑惑。他继续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藏品,并在本书中记录了他的发现……一段段神奇的故事。”
——艾拉·弗莱托,《科学星期五》
这是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愉快并且收获颇丰的阅读之旅。本书的每一章都给出一个物种或一个属的简要描述,这些物种或属通常是在博物馆标本收集几十年后才被正式命名的。其中大多数动物在过去15年内被描述和命名的,包括闪电蟑螂、隐身节蛙、来自新几内亚的西巴布亚鼠袋狸、红宝石海龙和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地点捕获的原子狼蛛。”
——《华尔街日报》
当肯普告诉我们这些鼓舞人心的发现时,你会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在自己身边的自然博物馆里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宝藏。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的物种。目前,据估计,地球上有1000万~3000万种物种,其中被命名的只有不到200万种。但令人惊讶的是,博物馆中有多达一半的标本被错误地分类了。很显然,还有许多分类学和系统学的研究要做。《失落的物种》引人入胜,有力地证明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体价值,以及研究这些藏品的重要性。
——GrrlScientist《福布斯》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一部分,克里斯托弗·肯普在本书中生动地讲述了保存下来的标本在基础研究中的价值。通过这些研究,他成功地将科学、历史和探险融合起来。
——“当代达尔文”,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Wilson)
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自然博物馆总共收藏了数十亿件珍贵的科学标本。在这些汇集了几个世纪的生命和文化的宝藏之中,每一件标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克里斯托弗·肯普生动地讲述了其中一些标本的故事,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主角,从卑微的线虫到强大的雷龙。他把这些标本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不仅可以展示地球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作为人类探索发现和*终研究的范例。任何对自然博物馆藏品感兴趣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它说明了这些藏品是如何收集的,以及我们可以从中知道什么。
——《策展人》作者兰斯·格兰德(Lance Grande)
自然博物馆中总是充满了惊喜——从飞狐到帝王蟹,它们在标本架上等待被人研究。克里斯托弗·肯普将这些标本以及收集和描述这些标本的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失落的物种》会让所有喜欢发现、探险的故事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也会被那些让关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读者所喜爱。
——《物种探寻者》作者理查德·康尼夫(Richard Conniff)
克里斯托弗·肯普精彩地讲述了自然博物馆藏品不为人知的故事,有很多新物种其实收藏在博物馆的标本抽屉和罐子里。喜欢探险并对博物馆、历史和生物多样性感兴趣的读者能在《失落的物种》中找到大量有趣的故事,这是一种有趣的、迷人的、对话式的阅读。
——《蝾螈之眼和青蛙之趾》作者马蒂·克伦普(Marty Crump)
前言
引言
几年前,田纳西大学的昆虫学家斯特利奥斯·查兹曼诺利斯(Stylianos Chatzimanolis),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借来了一盒未被归类的甲虫。分类学家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像从图书馆借书一样,从其他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借来研究材料。当时,查兹曼诺利斯借来的这些甲虫还未被世人所知——或者说还未被归类。之前有野外生物学家收集过这些甲虫,但没有人正式地描述它们。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当标本盒抵达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市时,查兹曼诺利斯发现有20只左右的甲虫标本被钉在盒子里。但有一只甲虫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首先,它看起来年龄大很多,是一只身长且腹部弯曲分段的隐翅甲,但身形尤其大,头部较宽且呈斑斓的绿色。
人们在1832年于阿根廷收集过这种昆虫的标本。当查兹曼诺利斯准备更近距离地观察标本和它泛黄的手写标签时,他发现这种甲虫早在“小猎犬号之旅”中就被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收集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描述它,在未命名的情况下被储藏起来,随后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数量巨大的昆虫藏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查尔斯·达尔文
最终,经历了180年的收藏之后,查兹曼诺利斯为其命名。这种甲虫和其他已知种类的甲虫完全不一样,因此查兹曼诺利斯不得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类别来将其囊括在内。他将这种甲虫命名为达尔文隐翅甲(Darwinilus sedarisi)。
现在这种甲虫已经有了名字,但核心问题依旧存在:命名重要吗?有必要给它命名吗?这个标本已经等待180年,为什么现在给它命名?其实这非常重要。
每个单一物种,都是地球生物多样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对自然界进行描述、分类和排序。当一个新物种被命名后,一系列其他工作就能得以迅速推进。通过研究一个新命名的物种及其近亲,生物学家能够得到对这个物种演化过程更深的理解;生态学家有机会得知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运作原理;环保研究者能够获得关于如何管理环境以保持种群数量的更深刻的见解。而要实现这一切,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物种的存在。
我们可以把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当作一支交响曲,每个物种代表了一个音符。一个单独的音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音符们聚集在一起并开始相互交融后就形成了主题。主题不断重复,慢慢构建成为乐章——丰盈的音乐片段,而不仅仅是每个部分的总和。但如果这页乐谱不完整呢?目前地球上被命名的物种约占总物种数的五分之一。想象一下,如果交响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时每五个音符才演奏一次,音符间隔处静寂无声,那该是什么样的情景?对主题的表达,对渐渐达到高潮的副歌的演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连地球生物多样性一半的组成部分都不了解,又何谈了解其丰富?
未知的物种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生物库中。据估算,新描述的哺乳动物的75%已经存在于这世界某个角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了。其他物种也是如此:从寄生虫、青蛙、鱼到珊瑚、苍蝇,从螃蟹、蛾到地衣、苔藓。2012年,一名研究者在哥本哈根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发现了一种以卵为食的海蛇。这种蛇名为摩西剑尾海蛇(Aipysurus mosaicus),在19世纪后期被收集,因其棕色与淡黄色的鳞片组成的马赛克纹路而得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被错误地归类和标记为另一种近似的物种,储存在罐中逾一个世纪。但由于它实在太与众不同了,一位眼尖的两栖爬行动物学者马上就发现了它。
据《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研究报告的作者估算,在7万多种还未被命名的开花植物中,有一半已经被收集,并储藏在植物标本室里,没有自己的名字。我们不难猜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仅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堪称包罗万物的昆虫部就储藏了约3000万件昆虫标本。标本数量太过巨大,分类学家和策展人很难对它们一一进行鉴别、分类和命名。
即使一种标本被鉴别出来,还是经常会被错误地归类和命名。《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2015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人员评估了21世纪植物标本室中标本命名的精确性。在被考察的标本中,基本一半的命名都是错误的。标本的收藏中充满了错误,这一问题不容小觑。如果标本的标签都是错的,那收集还有何用处?如果这些标本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物种又该怎么办?从1970年到2000年,植物标本室里的热带植物标本的数量翻了一番,但最近收集的大部分标本的命名都是错的,很多甚至没有名字。字迹已经模糊的手写标签上可能是“新物种?”这种令人欲知其名而不得的注释,或者干脆注释为“nov. sp.?”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对周遭这个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所知甚少,甚至不了解其皮毛。根据多数人估计,地球上大约有1000万种物种,但已经被命名的不超过200万种。剩余的物种还处于未被人类所知的状态。我们身处于由上千种互相联系的生物组成的广阔又极其复杂的生物系统中,但对这些生物互相沟通的方式和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一个物种——例如,一种其貌不扬的甲虫,或者一种蝙蝠、青蛙、兰花——从世界上消失,生态系统会受到什么影响。很有可能生态系统仍然照常运作,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进行平衡和适应。但怎么平衡适应?从中又能透露其余物种的什么信息?
换句话说,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对我们而言还是一个谜——它们既没有被描述,也没有被充分研究。命名一种普通的甲虫不会使它的生态角色发生任何变化,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连生物体的类别都不能确认,又如何理解生命的复杂性?一种连名字都没有的动物又如何能得到保护?
几百年来,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标本和它们最初的收集者帮助我们了解了周遭生物的多样性。如今,分类学家和生物学家每年对大约8万种物种进行描述。每天都有新物种被命名。这里面包括已经灭绝成为化石的物种和细菌、病毒之类的微生物。首先要确认正模标本,用以描述和定义整个物种的单个标本。生命之树上萌发新芽,是地球上大部分未知的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8万种新物种听起来是个庞大的数量,但其实只占了地球上所有物种中很小的一部分。
实际上,我们周围遍布着没有名字的物种。分类学家兼纽约州立环境科学与林业学院院长昆廷·惠勒(Quentin Wheeler)表示,现存的昆虫中我们可能至多命名了四分之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现新物种,从城市后院到遥远雨林,再到海洋深处。2016年9月,纽约罗契斯特大学的研究者给一种新发现的热带蚂蚁命名为“勒氏须蚁”(Lenomyrmex hoelldobleri)。他们在给名为“小恶魔”(Oophaga sylvatica)的色泽鲜艳、通体橘黄的毒蛙清洗胃部时发现了这种已经死了的体形较小的蚂蚁。这种蚂蚁生活在厄瓜多尔雨林。因为这只是一件标本,又是在青蛙的胃里发现的,没人准确地知道它们生活在哪里。鲨鱼学者大卫·艾伯特仅在一家中国台湾鱼市的鱼类标本中就命名了10种新的鲨鱼。不过更多情况下,生物学家收集了新物种后并未给它们命名。
当你去参观一些规模较大的著名藏品展(例如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加州自然科学院,或者位于莱顿、伦敦、巴黎、圣保罗的博物馆)时,你可能很难认识到公共空间之外的标本数量有多大。仅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蝙蝠标本就有超过25万件,而这只是更大、更全面的哺乳动物藏品中的一小部分。藏品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野外生物学家在偏远的地方工作,收集处理蝙蝠标本,用地理数据标注,然后把它们登记到标本藏品的名单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前往纽约研究和比较这些标本,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生物材料参考图书馆。或者,他们从博物馆里借来标本,就像查兹曼诺利斯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鞘翅目昆虫学家马克思·巴克莱(Max Barclay)监管,昆虫标本数量巨大,囊括了大约1000万种不同的昆虫标本,每年仅从这些标本中被命名的新甲虫物种就有超过1000种)借来甲虫标本。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估计有10亿件标本;夏威夷檀香山的毕夏普博物馆的昆虫藏品中有1400万件标本,包括36种蚊虫的正模标本;杜克大学的标本室有超过16万件苔藓标本;加州自然科学院的两栖爬行动物藏品包含了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万件已被分类的标本;史密斯学会中最古老的生物标本可以追溯到1504年。
一件标本从收集到被描述的时间被称为“橱柜时间”或“保存时间”。根据《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述,生物标本的平均橱柜时间大约为21年。命名和描述生物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但是少数情况下,一些标本的橱柜时间会延长很多,变得相当漫长。这些标本会被储藏在地下室、储藏柜、抽屉或装有固定剂的罐子里,等待长达50年或75年,有时会到100年甚至更久。它们的标签慢慢变黄褪色,收集它们的人也与世长辞了,但这些标本仍在等待。岁月流逝,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战争爆发,科技进步,保存着这些标本的国家的版图一再更改,这些标本藏品却丝毫未变。很多时候这些标本还和几百万件其他标本放在一起,使得它们更难被人发现。
一只未知类别的蜘蛛可能和其他50只已经为人熟知的常见蜘蛛放在一个烧瓶里。这种蜘蛛在一些细节处有明显的不同,这会告诉我们关于它来自的生态系统和演化进程的信息,但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它。它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在之后的某一天,一位研究生成为某一类蜘蛛的专家,他拿下瓶口的塞子,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
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的现状不容乐观,很多都岌岌可危。近年来,许多研究机构的经费都被削减了,致力于收藏的分类学家的人数也在下降。如今很多分类工作由进化生物学家完成,他们也没有资金支持。作为重要的管理人员,负责藏品保护和整理的策展人也在消失。举个例子,2001年,菲尔德博物馆有39名策展人,到2017年就只剩下21名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策展人的人数在1993年高达122名,到2017年只有81名,少了约30%。在过去,很多大型藏品管理机构都有一支保管队伍,每个策展人都是不同方面的专家:有三四个是哺乳动物学家,两位是鱼类学者。队伍里可能还有些知识渊博的昆虫学家,他们各自对某一类高度专门化的生物种群有着极高的兴趣和丰富的知识储备。现在这些专家的工作都被推到某一个藏品策展人身上,工作量之大使他感到不堪重负。而一些机构连藏品策展人的人数都不够。如今菲尔德博物馆的古植物、真菌、古人类、哺乳动物这几类重要的藏品都缺少策展人。
想象一个图书馆,里面装满了罕见而重要的书籍,却没有保管它们的人。
有时候一组自然标本的藏品会一起消失。在一些小型机构或学术部门,负责某类藏品的专家退休或去世后会遗留下上千件标本。少数情况下,这些被遗留下来的标本会被更大型的机构接收,纳入已经建立的藏品库中。但有些时候,它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很多机构开始进行数字化收藏,这一进程使全世界的研究者得以于千里之外评估标本。由自然科学基金会投资的美国生物标本数据化平台(Integrated Digitized Biocollections,iDigBio)就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全球合作的项目。结果令人惊叹:iDigBio建立了全世界超过7200万件不同标本的记录链接,包括从地衣、苔藓到低地大猩猩等各种生物的收集数据。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是另外一个项目:它是在各国政府支持下建立的数据库,旨在为全世界的机构数百万(如今已超过5000万)的数字化记录提供单一访问点。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昆虫数字化收藏工作,将每个标本转化为细节详细完备、能够旋转,从而可以从各角度观察的高分辨率球形影像。这意味着我现在可以坐在我的沙发上,观察从约旦河西岸采集的金龟子黄蜂(Chrysis Marqueti)闪闪发光的表面。或者,被刺穿在柏林的大头针上的半额叶蝉(Hemidictya frondosa)——一种奶油色的巴西蝉,保持着飞行的状态,展开着它那叶脉状的翅膀。
总的来说,数字化的藏品将增加分类知识,并有助于减少阻碍物种描述的障碍。鉴定的阻碍(也被称为分类学障碍)包括分类学家和策展人的不足、未确认的对象过多、研究兴趣不足以及对机构的支持的不断减少。如果对类似iDigBio的项目的资金支持停止或间歇性停止,那数字化努力的脚步也就停下了。
不管怎样,亲自接触标本的体验是不可替代的。手上标本的实感对大脑的触动是屏幕影像无法做到的。
对收藏界的许多人来说,自然标本藏品仿佛已随风飘逝。人们认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场所,光线昏暗,灰尘飞扬,如同一个模拟的世界。装满动物尸体的储物罐已经没有用处。毕竟,我们能从一只180年历史的甲虫标本上知道什么呢?
但现在标本藏品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地球上的生物不断变化,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分类学记录。许多科学家都表示,如今生物消失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速。据估算,现今生物灭绝的速度,比自然背景下的生物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之前的计算结果要快得多。我们已经进入了科学家所说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时代。对于一些物种来说,唯一能说明它们存在的只有那些少数被收集来的标本——自然界已经无法觅其踪迹。标本藏品有各种具体的用处,它们使研究者能够理解例如气候变化的复杂进程的影响,将某一地区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物种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利用标本收藏查明侵入物种的引进和生态系统出现的问题;鸟类学家可以利用标本数据追踪鸟类迁徙模式的变化;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25万件蝙蝠标本之类的生物标本,甚至可以让流行病学专家得以追踪埃博拉病毒(定期暴发于人类群体随后消失于动物宿主)之类的致命性动物传染病的暴发和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还记录着人类的行为。它们讲述着宏大的人类历史故事。一只来自加纳的无名天牛,或者一只越南蜗牛的长期中空的涡轮形背壳,就可以折射出长达300年的科学思想。这些标本来自世界各地:从海洋底部到火山内部,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婆罗洲的热带雨林,美国城市后院以及南极无边无际的脆弱的冻原地带。而未知的谜团就埋藏在这些大量的标本中。
它们或许会消失一段时间——有时是几个世纪,但终会被发现。
几年前,田纳西大学的昆虫学家斯特利奥斯·查兹曼诺利斯(Stylianos Chatzimanolis),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借来了一盒未被归类的甲虫。分类学家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像从图书馆借书一样,从其他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借来研究材料。当时,查兹曼诺利斯借来的这些甲虫还未被世人所知——或者说还未被归类。之前有野外生物学家收集过这些甲虫,但没有人正式地描述它们。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当标本盒抵达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市时,查兹曼诺利斯发现有20只左右的甲虫标本被钉在盒子里。但有一只甲虫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首先,它看起来年龄大很多,是一只身长且腹部弯曲分段的隐翅甲,但身形尤其大,头部较宽且呈斑斓的绿色。
人们在1832年于阿根廷收集过这种昆虫的标本。当查兹曼诺利斯准备更近距离地观察标本和它泛黄的手写标签时,他发现这种甲虫早在“小猎犬号之旅”中就被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收集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描述它,在未命名的情况下被储藏起来,随后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数量巨大的昆虫藏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查尔斯·达尔文
最终,经历了180年的收藏之后,查兹曼诺利斯为其命名。这种甲虫和其他已知种类的甲虫完全不一样,因此查兹曼诺利斯不得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类别来将其囊括在内。他将这种甲虫命名为达尔文隐翅甲(Darwinilus sedarisi)。
现在这种甲虫已经有了名字,但核心问题依旧存在:命名重要吗?有必要给它命名吗?这个标本已经等待180年,为什么现在给它命名?其实这非常重要。
每个单一物种,都是地球生物多样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对自然界进行描述、分类和排序。当一个新物种被命名后,一系列其他工作就能得以迅速推进。通过研究一个新命名的物种及其近亲,生物学家能够得到对这个物种演化过程更深的理解;生态学家有机会得知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运作原理;环保研究者能够获得关于如何管理环境以保持种群数量的更深刻的见解。而要实现这一切,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物种的存在。
我们可以把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当作一支交响曲,每个物种代表了一个音符。一个单独的音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音符们聚集在一起并开始相互交融后就形成了主题。主题不断重复,慢慢构建成为乐章——丰盈的音乐片段,而不仅仅是每个部分的总和。但如果这页乐谱不完整呢?目前地球上被命名的物种约占总物种数的五分之一。想象一下,如果交响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时每五个音符才演奏一次,音符间隔处静寂无声,那该是什么样的情景?对主题的表达,对渐渐达到高潮的副歌的演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连地球生物多样性一半的组成部分都不了解,又何谈了解其丰富?
未知的物种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生物库中。据估算,新描述的哺乳动物的75%已经存在于这世界某个角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了。其他物种也是如此:从寄生虫、青蛙、鱼到珊瑚、苍蝇,从螃蟹、蛾到地衣、苔藓。2012年,一名研究者在哥本哈根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发现了一种以卵为食的海蛇。这种蛇名为摩西剑尾海蛇(Aipysurus mosaicus),在19世纪后期被收集,因其棕色与淡黄色的鳞片组成的马赛克纹路而得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被错误地归类和标记为另一种近似的物种,储存在罐中逾一个世纪。但由于它实在太与众不同了,一位眼尖的两栖爬行动物学者马上就发现了它。
据《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研究报告的作者估算,在7万多种还未被命名的开花植物中,有一半已经被收集,并储藏在植物标本室里,没有自己的名字。我们不难猜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仅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堪称包罗万物的昆虫部就储藏了约3000万件昆虫标本。标本数量太过巨大,分类学家和策展人很难对它们一一进行鉴别、分类和命名。
即使一种标本被鉴别出来,还是经常会被错误地归类和命名。《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2015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人员评估了21世纪植物标本室中标本命名的精确性。在被考察的标本中,基本一半的命名都是错误的。标本的收藏中充满了错误,这一问题不容小觑。如果标本的标签都是错的,那收集还有何用处?如果这些标本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物种又该怎么办?从1970年到2000年,植物标本室里的热带植物标本的数量翻了一番,但最近收集的大部分标本的命名都是错的,很多甚至没有名字。字迹已经模糊的手写标签上可能是“新物种?”这种令人欲知其名而不得的注释,或者干脆注释为“nov. sp.?”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对周遭这个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所知甚少,甚至不了解其皮毛。根据多数人估计,地球上大约有1000万种物种,但已经被命名的不超过200万种。剩余的物种还处于未被人类所知的状态。我们身处于由上千种互相联系的生物组成的广阔又极其复杂的生物系统中,但对这些生物互相沟通的方式和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一个物种——例如,一种其貌不扬的甲虫,或者一种蝙蝠、青蛙、兰花——从世界上消失,生态系统会受到什么影响。很有可能生态系统仍然照常运作,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进行平衡和适应。但怎么平衡适应?从中又能透露其余物种的什么信息?
换句话说,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对我们而言还是一个谜——它们既没有被描述,也没有被充分研究。命名一种普通的甲虫不会使它的生态角色发生任何变化,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连生物体的类别都不能确认,又如何理解生命的复杂性?一种连名字都没有的动物又如何能得到保护?
几百年来,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标本和它们最初的收集者帮助我们了解了周遭生物的多样性。如今,分类学家和生物学家每年对大约8万种物种进行描述。每天都有新物种被命名。这里面包括已经灭绝成为化石的物种和细菌、病毒之类的微生物。首先要确认正模标本,用以描述和定义整个物种的单个标本。生命之树上萌发新芽,是地球上大部分未知的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8万种新物种听起来是个庞大的数量,但其实只占了地球上所有物种中很小的一部分。
实际上,我们周围遍布着没有名字的物种。分类学家兼纽约州立环境科学与林业学院院长昆廷·惠勒(Quentin Wheeler)表示,现存的昆虫中我们可能至多命名了四分之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现新物种,从城市后院到遥远雨林,再到海洋深处。2016年9月,纽约罗契斯特大学的研究者给一种新发现的热带蚂蚁命名为“勒氏须蚁”(Lenomyrmex hoelldobleri)。他们在给名为“小恶魔”(Oophaga sylvatica)的色泽鲜艳、通体橘黄的毒蛙清洗胃部时发现了这种已经死了的体形较小的蚂蚁。这种蚂蚁生活在厄瓜多尔雨林。因为这只是一件标本,又是在青蛙的胃里发现的,没人准确地知道它们生活在哪里。鲨鱼学者大卫·艾伯特仅在一家中国台湾鱼市的鱼类标本中就命名了10种新的鲨鱼。不过更多情况下,生物学家收集了新物种后并未给它们命名。
当你去参观一些规模较大的著名藏品展(例如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加州自然科学院,或者位于莱顿、伦敦、巴黎、圣保罗的博物馆)时,你可能很难认识到公共空间之外的标本数量有多大。仅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蝙蝠标本就有超过25万件,而这只是更大、更全面的哺乳动物藏品中的一小部分。藏品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野外生物学家在偏远的地方工作,收集处理蝙蝠标本,用地理数据标注,然后把它们登记到标本藏品的名单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前往纽约研究和比较这些标本,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生物材料参考图书馆。或者,他们从博物馆里借来标本,就像查兹曼诺利斯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鞘翅目昆虫学家马克思·巴克莱(Max Barclay)监管,昆虫标本数量巨大,囊括了大约1000万种不同的昆虫标本,每年仅从这些标本中被命名的新甲虫物种就有超过1000种)借来甲虫标本。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估计有10亿件标本;夏威夷檀香山的毕夏普博物馆的昆虫藏品中有1400万件标本,包括36种蚊虫的正模标本;杜克大学的标本室有超过16万件苔藓标本;加州自然科学院的两栖爬行动物藏品包含了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万件已被分类的标本;史密斯学会中最古老的生物标本可以追溯到1504年。
一件标本从收集到被描述的时间被称为“橱柜时间”或“保存时间”。根据《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述,生物标本的平均橱柜时间大约为21年。命名和描述生物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但是少数情况下,一些标本的橱柜时间会延长很多,变得相当漫长。这些标本会被储藏在地下室、储藏柜、抽屉或装有固定剂的罐子里,等待长达50年或75年,有时会到100年甚至更久。它们的标签慢慢变黄褪色,收集它们的人也与世长辞了,但这些标本仍在等待。岁月流逝,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战争爆发,科技进步,保存着这些标本的国家的版图一再更改,这些标本藏品却丝毫未变。很多时候这些标本还和几百万件其他标本放在一起,使得它们更难被人发现。
一只未知类别的蜘蛛可能和其他50只已经为人熟知的常见蜘蛛放在一个烧瓶里。这种蜘蛛在一些细节处有明显的不同,这会告诉我们关于它来自的生态系统和演化进程的信息,但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找到它。它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在之后的某一天,一位研究生成为某一类蜘蛛的专家,他拿下瓶口的塞子,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
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的现状不容乐观,很多都岌岌可危。近年来,许多研究机构的经费都被削减了,致力于收藏的分类学家的人数也在下降。如今很多分类工作由进化生物学家完成,他们也没有资金支持。作为重要的管理人员,负责藏品保护和整理的策展人也在消失。举个例子,2001年,菲尔德博物馆有39名策展人,到2017年就只剩下21名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策展人的人数在1993年高达122名,到2017年只有81名,少了约30%。在过去,很多大型藏品管理机构都有一支保管队伍,每个策展人都是不同方面的专家:有三四个是哺乳动物学家,两位是鱼类学者。队伍里可能还有些知识渊博的昆虫学家,他们各自对某一类高度专门化的生物种群有着极高的兴趣和丰富的知识储备。现在这些专家的工作都被推到某一个藏品策展人身上,工作量之大使他感到不堪重负。而一些机构连藏品策展人的人数都不够。如今菲尔德博物馆的古植物、真菌、古人类、哺乳动物这几类重要的藏品都缺少策展人。
想象一个图书馆,里面装满了罕见而重要的书籍,却没有保管它们的人。
有时候一组自然标本的藏品会一起消失。在一些小型机构或学术部门,负责某类藏品的专家退休或去世后会遗留下上千件标本。少数情况下,这些被遗留下来的标本会被更大型的机构接收,纳入已经建立的藏品库中。但有些时候,它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很多机构开始进行数字化收藏,这一进程使全世界的研究者得以于千里之外评估标本。由自然科学基金会投资的美国生物标本数据化平台(Integrated Digitized Biocollections,iDigBio)就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全球合作的项目。结果令人惊叹:iDigBio建立了全世界超过7200万件不同标本的记录链接,包括从地衣、苔藓到低地大猩猩等各种生物的收集数据。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GBIF)是另外一个项目:它是在各国政府支持下建立的数据库,旨在为全世界的机构数百万(如今已超过5000万)的数字化记录提供单一访问点。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昆虫数字化收藏工作,将每个标本转化为细节详细完备、能够旋转,从而可以从各角度观察的高分辨率球形影像。这意味着我现在可以坐在我的沙发上,观察从约旦河西岸采集的金龟子黄蜂(Chrysis Marqueti)闪闪发光的表面。或者,被刺穿在柏林的大头针上的半额叶蝉(Hemidictya frondosa)——一种奶油色的巴西蝉,保持着飞行的状态,展开着它那叶脉状的翅膀。
总的来说,数字化的藏品将增加分类知识,并有助于减少阻碍物种描述的障碍。鉴定的阻碍(也被称为分类学障碍)包括分类学家和策展人的不足、未确认的对象过多、研究兴趣不足以及对机构的支持的不断减少。如果对类似iDigBio的项目的资金支持停止或间歇性停止,那数字化努力的脚步也就停下了。
不管怎样,亲自接触标本的体验是不可替代的。手上标本的实感对大脑的触动是屏幕影像无法做到的。
对收藏界的许多人来说,自然标本藏品仿佛已随风飘逝。人们认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场所,光线昏暗,灰尘飞扬,如同一个模拟的世界。装满动物尸体的储物罐已经没有用处。毕竟,我们能从一只180年历史的甲虫标本上知道什么呢?
但现在标本藏品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地球上的生物不断变化,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分类学记录。许多科学家都表示,如今生物消失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速。据估算,现今生物灭绝的速度,比自然背景下的生物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之前的计算结果要快得多。我们已经进入了科学家所说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时代。对于一些物种来说,唯一能说明它们存在的只有那些少数被收集来的标本——自然界已经无法觅其踪迹。标本藏品有各种具体的用处,它们使研究者能够理解例如气候变化的复杂进程的影响,将某一地区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物种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利用标本收藏查明侵入物种的引进和生态系统出现的问题;鸟类学家可以利用标本数据追踪鸟类迁徙模式的变化;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25万件蝙蝠标本之类的生物标本,甚至可以让流行病学专家得以追踪埃博拉病毒(定期暴发于人类群体随后消失于动物宿主)之类的致命性动物传染病的暴发和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还记录着人类的行为。它们讲述着宏大的人类历史故事。一只来自加纳的无名天牛,或者一只越南蜗牛的长期中空的涡轮形背壳,就可以折射出长达300年的科学思想。这些标本来自世界各地:从海洋底部到火山内部,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婆罗洲的热带雨林,美国城市后院以及南极无边无际的脆弱的冻原地带。而未知的谜团就埋藏在这些大量的标本中。
它们或许会消失一段时间——有时是几个世纪,但终会被发现。
精彩书摘
其实,乌查岭鼠看起来就像只普通的老鼠。它的毛呈深棕色,到柔软的下腹部变为浅灰色,体形小,也没什么特点。就连2003年为它命名和描述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哺乳动物类的策展人罗伯特·沃斯(Robert Voss)都称它为“其貌不扬,外形像大鼠的蓝绿色老鼠”。
沃斯第一次见到乌查岭鼠是在1978年,当时他还是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沃斯说,当他在厄瓜多尔东北部的东科迪勒拉山高海拔的寒冷空气中发现这个物种时,他马上就知道,它如此突出且独特的牙齿说明它是一个新物种。
在描述物种的时候,像沃斯这样的野外生物学家经常使用色彩目录来精确描述标本的外部颜色,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颜色与纸上的色卡进行比较。他们的参考标准是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e)1975年出版的《自然主义者色彩指南》(Naturalist’s Color Guide)。沃斯运用史密斯的指南将这只老鼠描述如下:侧面为偏棕橄榄色(色码29),腹部为深中灰色(色码83),表面还有一抹浅中灰色(色码85)或蓝绿色(色码80)。它长而突出的门牙的釉质有几道橙色的条纹(色码17)。
沃斯在厄瓜多尔收集半水栖食虫动物标本,为他的论文研究做准备。他说,那里的环境很艰苦。拂晓时分,从山上流下的山涧两岸都结冰了,草丛上结着白霜。暴风雪毫无预兆地突然席卷而来,山丘变得模糊不清,当地牧民健壮的牲畜因遭受暴风雪袭击而死亡。即使是晴朗明媚的天气,过了正午之后,陡峭的山丘也会气温骤降。
在2003年对这种老鼠的正式描述中,沃斯写道:“我在这样陡峭且气候不稳定的山坡上找不到什么扎营的地方,湿漉漉的森林使我很难一次设下几天的陷阱线。”环境如此恶劣,难怪人们对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几乎一无所知。简单来说,没人想待在那里。那里既寒冷又潮湿,几乎没办法工作。想象一下:在45度的斜坡上工作,还不止一两天。就像沃斯在报告中所写:“很多进入厄瓜多尔东部进行标本探索的人,很快就顺坡而下到亚马孙平原更舒适的栖息地去收集标本了。”
但沃斯留在了坡上——世界的高脊,83色码的天空之下。
在大约14000英尺的地方,他开始寻找一种他称之为“体形较大、龅牙的啮齿动物”:Thomasomys ucucha。沃斯在树木矮小的亚高山雨林的林木线附近一处潮湿、长满苔藓、低矮树枝缠绕的名为“精灵森林”的地方安放了商业捕鼠器。他在冰封的河岸上设置了其他陷阱。几天后,他收集了43个这种动物的标本,带回美国,并把它们保存了起来。这些标本存放在位于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动物博物馆展出,直到2003年才被描述和命名。这物种的正模标本——一个1980年4月26日于帕帕亚克塔河谷(the valley of the Rio Papallacta)被捕获的成年雄性标本也在其中。
但是在1980年后的几年间沃斯一直忙于别的项目。1985年,他开始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有袋类动物的进化。沃斯总共参与了其他11种哺乳动物的命名。他说,描述一个新物种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和费力,需要研究者将许多物种与其近亲进行形态上的比较。一个新物种的独特性必须得到确凿的实证。
于是乌查岭鼠的标本一直在密歇根大学的某个抽屉里,可能有些人觉得一个生物从收集到描述要经历25年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25年只是平均时间。乌查岭鼠等待的时间要长得多。
沃斯最终将注意力转向20世纪70年代在厄瓜多尔收集的未命名标本。他从密歇根大学借来这些标本,这是分类学研究中的一种常见做法。与此同时,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寻了大量庞杂的哺乳动物标本,从中挑选了一些近亲物种,与他从密歇根带回的标本进行比较。他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物种标本,但他也有意外的收获:他找到了之前的老鼠。有3只这类老鼠的标本:偏棕橄榄色的侧面,灰色的腹部,有几道橙色条纹的牙齿。
这些标本都由业余野外生物学家卢多维奇·索德斯特伦(Ludovic Soderstrom)于1903年在厄瓜多尔收集——沃斯说,或者更有可能,是卢多维奇·索德斯特伦训练的众多厄瓜多尔原住民中的一位为他收集的。索德斯特伦于1927年去世,此前的40多年间,他雇用了一支小型的收集标本的队伍,收集在陡峭的地形间遇到的所有生物。索德斯特伦是一名英国外交官,曾在英国驻基多领事馆工作,在秘鲁东部和西部低地的乡村拥有大片地产。他将标本收集者们为他收集到的大量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出售和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这批物种种类繁多:1896年,他把厄瓜多尔哺乳动物的标本送到大英博物馆;1900年,把蜂鸟的外皮送到佩思郡自然历史博物馆;把西番莲种子送到美国农业部;把柔软的烟色鼩负鼠(Caenolestes fuliginosus)的标本送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在1914年把一只黄领唐纳雀(Tangara pulcherrima)标本送到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他将后来命名为Opuntia soederstromiana的厄瓜多尔仙人掌活体标本送到卡内基科学研究所,但这些仙人掌在运送途中都死亡了。索德斯特伦还把新热带鹿的标本送到菲尔德博物馆,把种子送到英国皇家植物园,就这样不断地送下去。
沃斯第一次见到乌查岭鼠是在1978年,当时他还是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沃斯说,当他在厄瓜多尔东北部的东科迪勒拉山高海拔的寒冷空气中发现这个物种时,他马上就知道,它如此突出且独特的牙齿说明它是一个新物种。
在描述物种的时候,像沃斯这样的野外生物学家经常使用色彩目录来精确描述标本的外部颜色,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颜色与纸上的色卡进行比较。他们的参考标准是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e)1975年出版的《自然主义者色彩指南》(Naturalist’s Color Guide)。沃斯运用史密斯的指南将这只老鼠描述如下:侧面为偏棕橄榄色(色码29),腹部为深中灰色(色码83),表面还有一抹浅中灰色(色码85)或蓝绿色(色码80)。它长而突出的门牙的釉质有几道橙色的条纹(色码17)。
沃斯在厄瓜多尔收集半水栖食虫动物标本,为他的论文研究做准备。他说,那里的环境很艰苦。拂晓时分,从山上流下的山涧两岸都结冰了,草丛上结着白霜。暴风雪毫无预兆地突然席卷而来,山丘变得模糊不清,当地牧民健壮的牲畜因遭受暴风雪袭击而死亡。即使是晴朗明媚的天气,过了正午之后,陡峭的山丘也会气温骤降。
在2003年对这种老鼠的正式描述中,沃斯写道:“我在这样陡峭且气候不稳定的山坡上找不到什么扎营的地方,湿漉漉的森林使我很难一次设下几天的陷阱线。”环境如此恶劣,难怪人们对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几乎一无所知。简单来说,没人想待在那里。那里既寒冷又潮湿,几乎没办法工作。想象一下:在45度的斜坡上工作,还不止一两天。就像沃斯在报告中所写:“很多进入厄瓜多尔东部进行标本探索的人,很快就顺坡而下到亚马孙平原更舒适的栖息地去收集标本了。”
但沃斯留在了坡上——世界的高脊,83色码的天空之下。
在大约14000英尺的地方,他开始寻找一种他称之为“体形较大、龅牙的啮齿动物”:Thomasomys ucucha。沃斯在树木矮小的亚高山雨林的林木线附近一处潮湿、长满苔藓、低矮树枝缠绕的名为“精灵森林”的地方安放了商业捕鼠器。他在冰封的河岸上设置了其他陷阱。几天后,他收集了43个这种动物的标本,带回美国,并把它们保存了起来。这些标本存放在位于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动物博物馆展出,直到2003年才被描述和命名。这物种的正模标本——一个1980年4月26日于帕帕亚克塔河谷(the valley of the Rio Papallacta)被捕获的成年雄性标本也在其中。
但是在1980年后的几年间沃斯一直忙于别的项目。1985年,他开始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有袋类动物的进化。沃斯总共参与了其他11种哺乳动物的命名。他说,描述一个新物种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和费力,需要研究者将许多物种与其近亲进行形态上的比较。一个新物种的独特性必须得到确凿的实证。
于是乌查岭鼠的标本一直在密歇根大学的某个抽屉里,可能有些人觉得一个生物从收集到描述要经历25年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25年只是平均时间。乌查岭鼠等待的时间要长得多。
沃斯最终将注意力转向20世纪70年代在厄瓜多尔收集的未命名标本。他从密歇根大学借来这些标本,这是分类学研究中的一种常见做法。与此同时,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寻了大量庞杂的哺乳动物标本,从中挑选了一些近亲物种,与他从密歇根带回的标本进行比较。他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物种标本,但他也有意外的收获:他找到了之前的老鼠。有3只这类老鼠的标本:偏棕橄榄色的侧面,灰色的腹部,有几道橙色条纹的牙齿。
这些标本都由业余野外生物学家卢多维奇·索德斯特伦(Ludovic Soderstrom)于1903年在厄瓜多尔收集——沃斯说,或者更有可能,是卢多维奇·索德斯特伦训练的众多厄瓜多尔原住民中的一位为他收集的。索德斯特伦于1927年去世,此前的40多年间,他雇用了一支小型的收集标本的队伍,收集在陡峭的地形间遇到的所有生物。索德斯特伦是一名英国外交官,曾在英国驻基多领事馆工作,在秘鲁东部和西部低地的乡村拥有大片地产。他将标本收集者们为他收集到的大量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出售和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这批物种种类繁多:1896年,他把厄瓜多尔哺乳动物的标本送到大英博物馆;1900年,把蜂鸟的外皮送到佩思郡自然历史博物馆;把西番莲种子送到美国农业部;把柔软的烟色鼩负鼠(Caenolestes fuliginosus)的标本送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在1914年把一只黄领唐纳雀(Tangara pulcherrima)标本送到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他将后来命名为Opuntia soederstromiana的厄瓜多尔仙人掌活体标本送到卡内基科学研究所,但这些仙人掌在运送途中都死亡了。索德斯特伦还把新热带鹿的标本送到菲尔德博物馆,把种子送到英国皇家植物园,就这样不断地送下去。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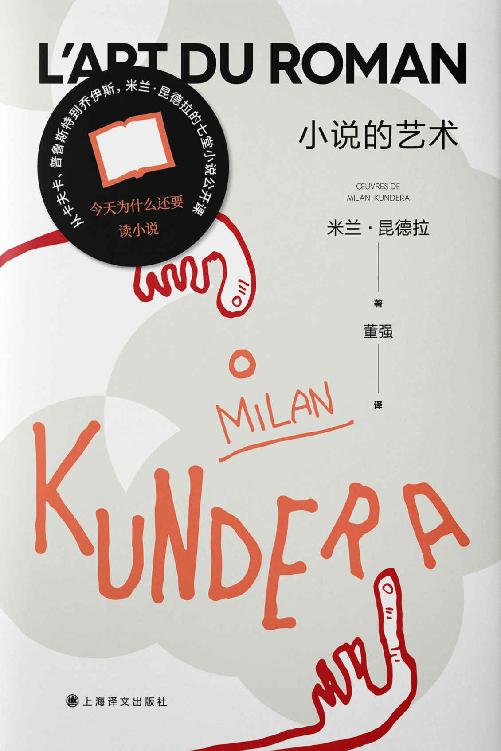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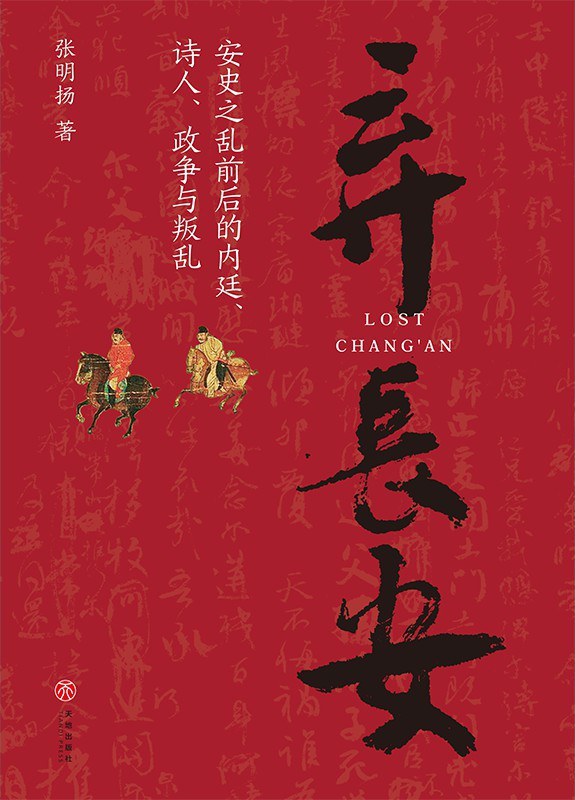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