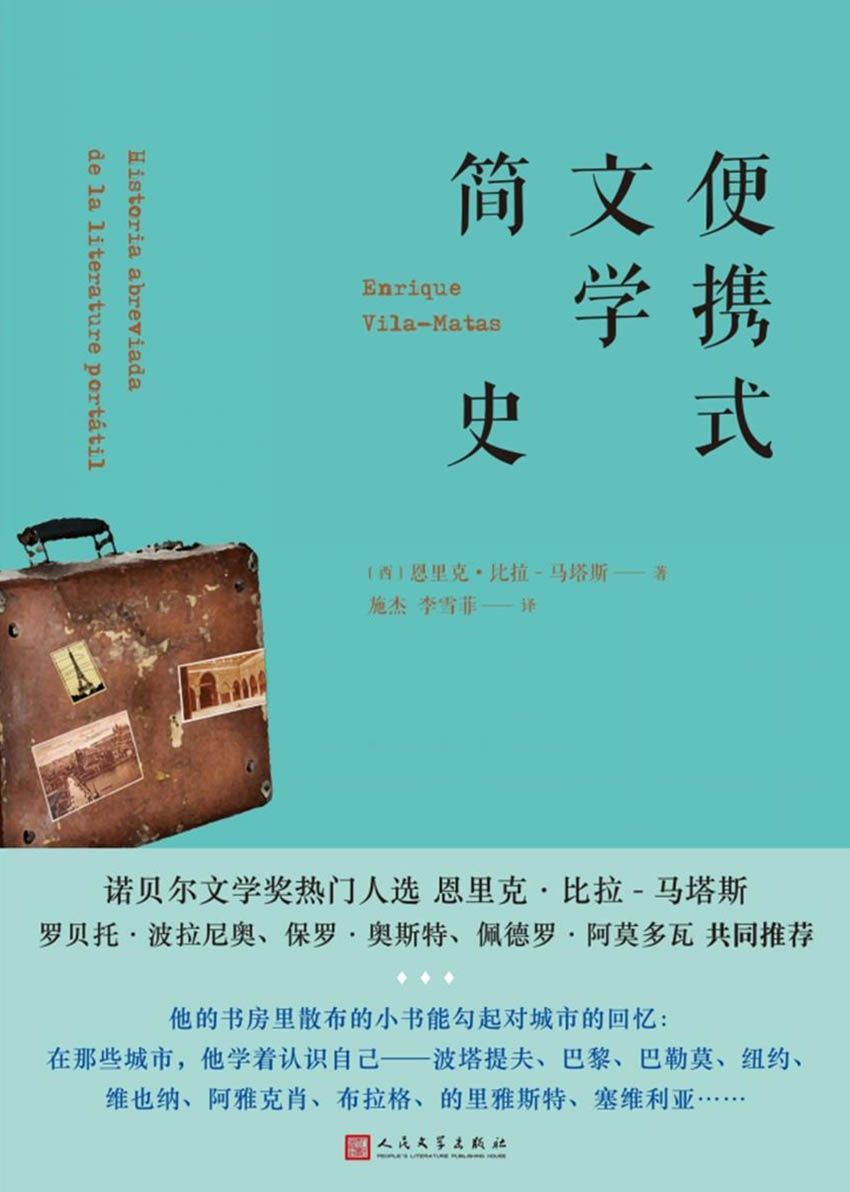
《便携式文学简史》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成名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塞尔·杜尚、瓦尔特·本雅明、乔治·安太尔、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乔治亚·欧姬芙、曼·雷、保罗·克利……这些杰出的艺术家、哲学家和作家都是“项狄社”的成员。
想要加入“项狄社”,需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其全部着作不得沉重,应轻易就能装进手提箱;其次,须是完美的光棍机器。
从苏黎世镜子街1号(伏尔泰酒馆前)到布拉格、塞维利亚,项狄们走得越来越远。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罗贝托·波拉尼奥、保罗·奥斯特、佩德罗·阿莫多瓦 共同推荐
他的书房里散布的小书能勾起对城市的回忆:
在那些城市,他学着认识自己——波塔提夫、巴黎、巴勒莫、纽约、
维也纳、阿雅克肖、布拉格、的里雅斯特、塞维利亚……
作者简介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1948— ),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比拉-马塔斯出生于巴塞罗那,1968年为逃离佛朗哥政府的独裁统治而移居巴黎。一生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二十余部小说和散文集,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曾荣获多个知名文学奖项,如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西班牙巴塞罗那城市文学奖、西班牙文学批评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等,并因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前言/序言
序
一九二四年残冬,在尼采悟得永恒轮回的那块巨石上,俄罗斯作家安德烈?别雷因体验超意识岩浆不可扼制的升腾而精神崩溃。同一天同一时刻,于此不远,音乐家埃德加?瓦雷兹在戏仿阿波利奈尔预备随军出征时猝然坠马。
在我看来,这两个场景便是支撑起便携式文学史的基柱。一部初生的欧洲史,轻便得如同保罗?莫朗乘坐豪华列车穿行在灯火辉煌的夜晚之欧洲时携带的书柜-旅行箱:马塞尔?杜尚正是从这个移动书柜中得到灵感,创造了他“手提箱里的盒子”——无疑是艺术领域对“便携”一词最天才的赞颂。这些箱中之盒装载着杜尚所有作品微缩版的复制件,不久即成了便携式文学的回文、元老项狄们自我认知的标志。
数月后,经过细微修改(手提箱里的盒子被安上了一把发梳作为按扣)的杜尚回文被雅克?瑞冈特拿来表征——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学史中的轻便崇拜”。此人或因其昭然异端的性格受到激赞,同时掀起了一轮对杜尚回文更新也更放肆的雪崩式的亵渎——足证项狄秘社最初的成员对离经叛道的恒常热爱。
那段日子,在元老项狄们中存在一种普遍的恐惧,生怕手提箱盒会被任意鸡鸣狗盗之徒盗走,于是瓦尔特?本雅明成功设计出了一种称书机,这种我们如今仍在使用的以其姓氏命名的机器能对无法装载的书籍做出绝对精准的判断,那些无法装载的书籍即便经历层层伪装亦难逃脱“不便携带”的评定。
并非偶然的是,本雅明称书机的发明者,究其文字的独创性,大半缘于他微观的视野以及对透视理论的不懈统御。“最吸引他的是那些微小的事物。”其密友格尔斯霍姆?肖勒姆这样写道。瓦尔特?本雅明喜欢旧玩具、邮票、明信片,以及装在玻璃球里、摇一摇便下起雪的仿真冬景。
本雅明的字体也近乎微型,他毕生未能实现的野心是将一百行文字塞进一张纸里。肖勒姆说,他初次去巴黎访问本雅明时,后者把他拖到克吕尼博物馆,只为了让他看一看犹太仪礼器具物品展中的两颗谷粒:一位同道中人在上面刻下了完整版的“以色列啊,你要听”。
瓦尔特?本雅明亦可谓杜尚同道。两人都居无定所,永远在路上,同是艺术界的流亡者,也是身背物什——亦即身背激情——的收藏家。两人都熟知,迷你化就是制造便携:这才是流浪汉与漂泊者拥有物件的理想方式。
但迷你化也是隐藏。譬如杜尚,他一直被极小所吸引,即那些须经解译的东西:纹章、手书、回文。对他来说,迷你化也意味着产出无用:“微缩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被免除了含义。它的小既是整体也是片段。对小的热爱是孩童的热爱。”
孩童如卡夫卡的目光。众人皆知他为进入父权社会所挑起的死斗,但他只能接受在继续充当无责任的幼童的前提下达成他的目的。
无责任的幼童,这是便携式作家举手投足的一贯标准。从第一刻起他们便规定了加入项狄秘社的基本要求:保持单身,至少得有相称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像马塞尔?杜尚理解的光棍机器一般运行。是时他刚得知——正是从埃德加?瓦雷兹那里——安德烈?别雷的精神崩溃:“那一瞬,也不知为什么,我不再聆听瓦雷兹的话,而是想到,人不该给生命太多负载、太多事去做,所谓女人、小孩、乡村小屋、汽车,等等。我庆幸自己醒悟得早,让我轻松做了那么久的单身汉,不用面对生活中那些再普通不过的苦难。归根结底,这才是最主要的。”
杜尚恰恰就在瓦雷兹谈及别雷在永恒轮回的巨石上精神崩溃的那一刻憬悟,此事着实令人称怪。人们不免自问,别雷的神经问题与杜尚如无责任的孩童般做着白日梦的力保独身的决定有何干系。问题太难,实际上没法知道答案。最可能的是它们之间不存一点联系,只是杜尚,在没有任何记忆或联想能够当即做出解释的情况下,陡然看见一个独身汉出现在眼前,他无依无凭、无法交往、痴狂谵妄,全然一名便携式艺术家,或换句话说,一个可以被泰然带往任何地方的人的形象。
总之说到头,唯一清楚的就是,瓦雷兹的坠马,别雷的崩溃,以及一名无依无凭、无法交往、痴狂谵妄的独身艺术家在杜尚视象中的意外显现,即是奠定项狄秘社基础的支柱。
除了必须具有较高程度的疯癫之外,他们还拟定了秘社成员的另两项基本要求:首先,其作品不得沉重,应轻易就能置于手提箱中;另一个要求则是,要如光棍机器一般运转。尽管并非必须,同样推荐秘社成员们拥有一些被认为是典型的项狄特征:创新精神、极端性观念、胸无大志、漂泊不倦、难以与双重自我共处、关心黑人地位和致力于蛮横艺术。
蛮横中包含着能击溃旧有机制的超人的行动力与骄傲的自主性,在强大却缓慢的敌人面前以快速制胜。项狄们自此便把“将便携式密谋推演为对以疾雷迅光之势出现并消失的事物的无上礼赞”视作最高追求。因此,以“为合谋而合谋”为首要特征的项狄密谋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瓦雷兹坠马与别雷崩溃不过三年之后,一九二七年,在塞维利亚的贡戈拉纪念日上,撒旦主义者阿莱斯特?克劳利以戏谑的表情解散了这个便携式结社。
克劳利放飞项狄雄鹰的几年之后,而今的我宣告,便携式结社的生命远远超过其创立者的想象,它联结着这个在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秘密社团的所有成员。
下面的书页里讲述的便是那些冒着生命——至少也是神经错乱——的风险也要实现他们的作品的人;犄角、斗牛的威胁,它们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在那些作品中。我们会认识他们;正因他们,如今吾辈才能空前轻易地揭去那些家伙的假面,正如赫尔曼?布洛赫所述:“不是说他们是坏作家,他们是罪犯。”
我们会认识造就了这本关于史上最快乐、最反复无常、最神经错乱的神秘结社——它已烟消云散——的小说的人:消费了无数烟草与咖啡的迷醉作家,在生活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无依无凭、谵妄的英雄,书写的热爱者——当书写成为了他们最有趣同时也是最不容调和的经历。
一九二四年残冬,在尼采悟得永恒轮回的那块巨石上,俄罗斯作家安德烈?别雷因体验超意识岩浆不可扼制的升腾而精神崩溃。同一天同一时刻,于此不远,音乐家埃德加?瓦雷兹在戏仿阿波利奈尔预备随军出征时猝然坠马。
在我看来,这两个场景便是支撑起便携式文学史的基柱。一部初生的欧洲史,轻便得如同保罗?莫朗乘坐豪华列车穿行在灯火辉煌的夜晚之欧洲时携带的书柜-旅行箱:马塞尔?杜尚正是从这个移动书柜中得到灵感,创造了他“手提箱里的盒子”——无疑是艺术领域对“便携”一词最天才的赞颂。这些箱中之盒装载着杜尚所有作品微缩版的复制件,不久即成了便携式文学的回文、元老项狄们自我认知的标志。
数月后,经过细微修改(手提箱里的盒子被安上了一把发梳作为按扣)的杜尚回文被雅克?瑞冈特拿来表征——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学史中的轻便崇拜”。此人或因其昭然异端的性格受到激赞,同时掀起了一轮对杜尚回文更新也更放肆的雪崩式的亵渎——足证项狄秘社最初的成员对离经叛道的恒常热爱。
那段日子,在元老项狄们中存在一种普遍的恐惧,生怕手提箱盒会被任意鸡鸣狗盗之徒盗走,于是瓦尔特?本雅明成功设计出了一种称书机,这种我们如今仍在使用的以其姓氏命名的机器能对无法装载的书籍做出绝对精准的判断,那些无法装载的书籍即便经历层层伪装亦难逃脱“不便携带”的评定。
并非偶然的是,本雅明称书机的发明者,究其文字的独创性,大半缘于他微观的视野以及对透视理论的不懈统御。“最吸引他的是那些微小的事物。”其密友格尔斯霍姆?肖勒姆这样写道。瓦尔特?本雅明喜欢旧玩具、邮票、明信片,以及装在玻璃球里、摇一摇便下起雪的仿真冬景。
本雅明的字体也近乎微型,他毕生未能实现的野心是将一百行文字塞进一张纸里。肖勒姆说,他初次去巴黎访问本雅明时,后者把他拖到克吕尼博物馆,只为了让他看一看犹太仪礼器具物品展中的两颗谷粒:一位同道中人在上面刻下了完整版的“以色列啊,你要听”。
瓦尔特?本雅明亦可谓杜尚同道。两人都居无定所,永远在路上,同是艺术界的流亡者,也是身背物什——亦即身背激情——的收藏家。两人都熟知,迷你化就是制造便携:这才是流浪汉与漂泊者拥有物件的理想方式。
但迷你化也是隐藏。譬如杜尚,他一直被极小所吸引,即那些须经解译的东西:纹章、手书、回文。对他来说,迷你化也意味着产出无用:“微缩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被免除了含义。它的小既是整体也是片段。对小的热爱是孩童的热爱。”
孩童如卡夫卡的目光。众人皆知他为进入父权社会所挑起的死斗,但他只能接受在继续充当无责任的幼童的前提下达成他的目的。
无责任的幼童,这是便携式作家举手投足的一贯标准。从第一刻起他们便规定了加入项狄秘社的基本要求:保持单身,至少得有相称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像马塞尔?杜尚理解的光棍机器一般运行。是时他刚得知——正是从埃德加?瓦雷兹那里——安德烈?别雷的精神崩溃:“那一瞬,也不知为什么,我不再聆听瓦雷兹的话,而是想到,人不该给生命太多负载、太多事去做,所谓女人、小孩、乡村小屋、汽车,等等。我庆幸自己醒悟得早,让我轻松做了那么久的单身汉,不用面对生活中那些再普通不过的苦难。归根结底,这才是最主要的。”
杜尚恰恰就在瓦雷兹谈及别雷在永恒轮回的巨石上精神崩溃的那一刻憬悟,此事着实令人称怪。人们不免自问,别雷的神经问题与杜尚如无责任的孩童般做着白日梦的力保独身的决定有何干系。问题太难,实际上没法知道答案。最可能的是它们之间不存一点联系,只是杜尚,在没有任何记忆或联想能够当即做出解释的情况下,陡然看见一个独身汉出现在眼前,他无依无凭、无法交往、痴狂谵妄,全然一名便携式艺术家,或换句话说,一个可以被泰然带往任何地方的人的形象。
总之说到头,唯一清楚的就是,瓦雷兹的坠马,别雷的崩溃,以及一名无依无凭、无法交往、痴狂谵妄的独身艺术家在杜尚视象中的意外显现,即是奠定项狄秘社基础的支柱。
除了必须具有较高程度的疯癫之外,他们还拟定了秘社成员的另两项基本要求:首先,其作品不得沉重,应轻易就能置于手提箱中;另一个要求则是,要如光棍机器一般运转。尽管并非必须,同样推荐秘社成员们拥有一些被认为是典型的项狄特征:创新精神、极端性观念、胸无大志、漂泊不倦、难以与双重自我共处、关心黑人地位和致力于蛮横艺术。
蛮横中包含着能击溃旧有机制的超人的行动力与骄傲的自主性,在强大却缓慢的敌人面前以快速制胜。项狄们自此便把“将便携式密谋推演为对以疾雷迅光之势出现并消失的事物的无上礼赞”视作最高追求。因此,以“为合谋而合谋”为首要特征的项狄密谋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瓦雷兹坠马与别雷崩溃不过三年之后,一九二七年,在塞维利亚的贡戈拉纪念日上,撒旦主义者阿莱斯特?克劳利以戏谑的表情解散了这个便携式结社。
克劳利放飞项狄雄鹰的几年之后,而今的我宣告,便携式结社的生命远远超过其创立者的想象,它联结着这个在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秘密社团的所有成员。
下面的书页里讲述的便是那些冒着生命——至少也是神经错乱——的风险也要实现他们的作品的人;犄角、斗牛的威胁,它们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在那些作品中。我们会认识他们;正因他们,如今吾辈才能空前轻易地揭去那些家伙的假面,正如赫尔曼?布洛赫所述:“不是说他们是坏作家,他们是罪犯。”
我们会认识造就了这本关于史上最快乐、最反复无常、最神经错乱的神秘结社——它已烟消云散——的小说的人:消费了无数烟草与咖啡的迷醉作家,在生活的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无依无凭、谵妄的英雄,书写的热爱者——当书写成为了他们最有趣同时也是最不容调和的经历。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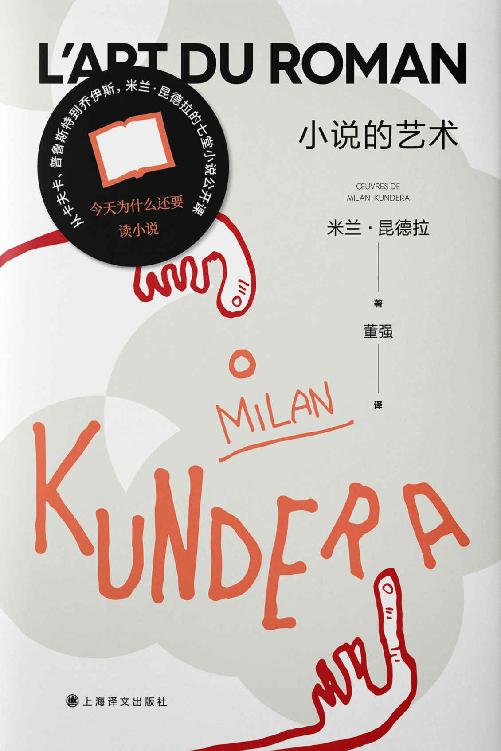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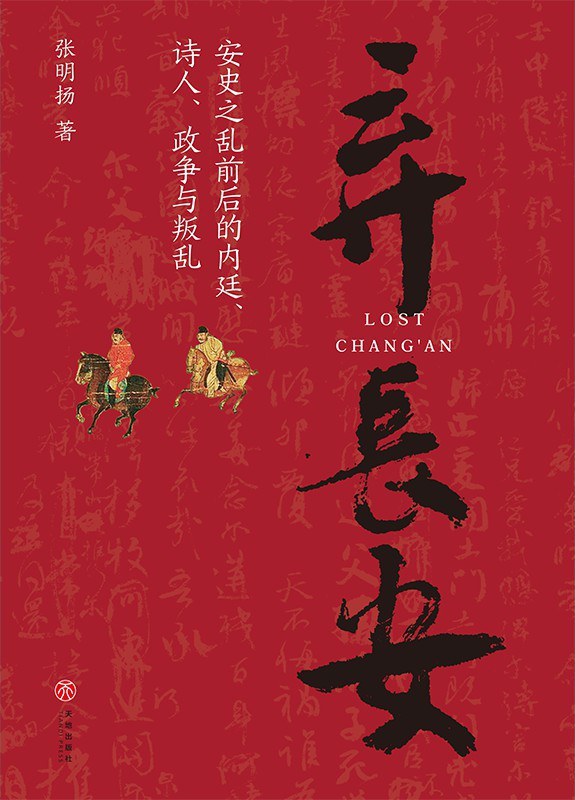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