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性》作者波伏瓦生前从未公开的小说手稿首度面世,以少女时代挚友扎扎为原型,悼念她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友谊。
九岁那年,希尔维初次遇见与她同岁的女孩安德蕾。她从未见过如此酷的女孩。与乖顺的“好学生”希尔维不同,安德蕾聪慧却叛逆,对一切若即若离。她经历过可怕的烧伤,身上带着火的印记。为了拒绝参加社交活动,她不惜用斧头砍伤自己。
她们变得形影不离。这感情炽烈、深入灵魂。从一起违抗学校秩序开始,循规蹈矩的希尔维一步步走向自由;生而不羁的安德蕾,却在家庭和礼法的约束下,步步挣扎,逐渐成为困兽。
编辑推荐
◎《第二性》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生前从未公开的小说手稿首度面世
◎一部差点被萨特“判死刑”的小说,以波伏瓦少女时代挚友扎扎为原型,悼念她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友谊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有两次失去对她影响至深,一次是丧失对上帝的信仰,一次是挚友扎扎的去世。她曾说:“我们一起与摆在我们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相信她的死就是我为自己的自由付出的代价。”
◎波伏瓦文学遗产继承人、其养女希尔维·勒邦·德·波伏瓦作序,收录波伏瓦珍贵影像资料、手稿及信件
◎《形影不离》写于《第二性》出版后第五年,波伏瓦生前毁掉了许多从未发表的作品,却始终没有毁掉这一部。她曾表示,她之所以写那些后来让她成名的书,是为了有机会讲述她的少女时代
◎两位特立独行、内心叛逆的女孩纠缠一生的友谊,只有女性懂得女性的挣扎与苦楚,女性是女性坚不可摧的精神同盟
◎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博士、第五届傅雷翻译奖新人奖获得者曹冬雪用心翻译,译文准确、优美
◎读这本书吧,然后尽情哭吧,亲爱的读者。因为起初它也浸染了作者的眼泪: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从哭泣开始。看起来,尽管外表严肃冷峻,波伏瓦心中从未停止哭泣,因为失去扎扎。也许她如此勤奋地工作,以成为后来的她,是某种形式的纪念:她必须竭尽全力表达自己,因为扎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使女的故事》作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一部差点被萨特“判死刑”的小说,以波伏瓦少女时代挚友扎扎为原型,悼念她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友谊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有两次失去对她影响至深,一次是丧失对上帝的信仰,一次是挚友扎扎的去世。她曾说:“我们一起与摆在我们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相信她的死就是我为自己的自由付出的代价。”
◎波伏瓦文学遗产继承人、其养女希尔维·勒邦·德·波伏瓦作序,收录波伏瓦珍贵影像资料、手稿及信件
◎《形影不离》写于《第二性》出版后第五年,波伏瓦生前毁掉了许多从未发表的作品,却始终没有毁掉这一部。她曾表示,她之所以写那些后来让她成名的书,是为了有机会讲述她的少女时代
◎两位特立独行、内心叛逆的女孩纠缠一生的友谊,只有女性懂得女性的挣扎与苦楚,女性是女性坚不可摧的精神同盟
◎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博士、第五届傅雷翻译奖新人奖获得者曹冬雪用心翻译,译文准确、优美
◎读这本书吧,然后尽情哭吧,亲爱的读者。因为起初它也浸染了作者的眼泪: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从哭泣开始。看起来,尽管外表严肃冷峻,波伏瓦心中从未停止哭泣,因为失去扎扎。也许她如此勤奋地工作,以成为后来的她,是某种形式的纪念:她必须竭尽全力表达自己,因为扎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使女的故事》作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目录
引言
序言
插图
致词
第一章
第二章
译后记
影像资料
序言
插图
致词
第一章
第二章
译后记
影像资料
媒体评论
从《形影不离》来看,波伏瓦青年时期对她影响至深的关系不是和萨特的。没有扎扎,可能就不会有《第二性》。至少,西蒙娜,因此没有自我牺牲于传统和家庭的祭坛上。
——《纽约时报书评》
《形影不离》展示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另一面——来自伟大的法国传统中的浪漫主义。对我来说,令人惊喜的是波伏瓦写小说的天分。温柔,亦有些调皮,波伏瓦使用了丰富的元素:自然、家庭、贫穷和富有,以及来自物质世界的一切——衣服、饰品、锅碗瓢盆。波伏瓦以她的艺术为抵押,承诺有一天扎扎将复活。这部最后的、未发表的小说像一个奇迹,从冰冷的记忆中唤醒了死者,唤醒了青春的率真,唤醒了全部的爱与失去。波伏娃闪亮的文字通过回忆往昔来回报今天的我们。
——《华尔街日报》
随着希尔维的脚步,我们作为读者,时而驻足,时而停留,见证了崇敬之情涌现。这是一种细密的、并不私密的爱,引人遐想,但永远说不清,也无法界定,人的心灵无限宽广……在《形影不离》中,朋友与恋人、异性之爱与同性之爱之间的区别,在生者对自己死去的朋友的爱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纽约客》
读这本书吧,尽情哭吧,亲爱的读者。因为起初它也浸染了作者的眼泪: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从哭泣开始。看起来,尽管外表严肃冷峻,波伏瓦心中从未停止哭泣,因为失去扎扎。也许她如此勤奋地工作,以成为后来的她,是某种形式的纪念:她必须竭尽全力表达自己,因为扎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使女的故事》作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形影不离》就像许多注定是悲剧的爱情故事一样,痛苦和甜蜜都很炽烈。短暂而热烈。本书扩大了我们对这位二十世纪女权泰斗的认知,以出人意料的温柔、不设防的方式展现了她。除此之外,这还是一本令人触动的女性成长小说。
——《哈珀杂志》
这本小说精彩绝伦、充满智性、满怀激情,在很多方面都仿佛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这样当代作品的前兆之作。
——《奥普拉日报》
对女性友谊、自我和失去的描写感人至深。
——《柯克斯评论》
这位女权先锋写出了女性友谊的复杂性,令人耳目一新。波伏瓦在对小说的驾驭能力进一步展示了她的精湛技艺。
——《出版人周刊》
——《纽约时报书评》
《形影不离》展示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另一面——来自伟大的法国传统中的浪漫主义。对我来说,令人惊喜的是波伏瓦写小说的天分。温柔,亦有些调皮,波伏瓦使用了丰富的元素:自然、家庭、贫穷和富有,以及来自物质世界的一切——衣服、饰品、锅碗瓢盆。波伏瓦以她的艺术为抵押,承诺有一天扎扎将复活。这部最后的、未发表的小说像一个奇迹,从冰冷的记忆中唤醒了死者,唤醒了青春的率真,唤醒了全部的爱与失去。波伏娃闪亮的文字通过回忆往昔来回报今天的我们。
——《华尔街日报》
随着希尔维的脚步,我们作为读者,时而驻足,时而停留,见证了崇敬之情涌现。这是一种细密的、并不私密的爱,引人遐想,但永远说不清,也无法界定,人的心灵无限宽广……在《形影不离》中,朋友与恋人、异性之爱与同性之爱之间的区别,在生者对自己死去的朋友的爱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纽约客》
读这本书吧,尽情哭吧,亲爱的读者。因为起初它也浸染了作者的眼泪: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从哭泣开始。看起来,尽管外表严肃冷峻,波伏瓦心中从未停止哭泣,因为失去扎扎。也许她如此勤奋地工作,以成为后来的她,是某种形式的纪念:她必须竭尽全力表达自己,因为扎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使女的故事》作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形影不离》就像许多注定是悲剧的爱情故事一样,痛苦和甜蜜都很炽烈。短暂而热烈。本书扩大了我们对这位二十世纪女权泰斗的认知,以出人意料的温柔、不设防的方式展现了她。除此之外,这还是一本令人触动的女性成长小说。
——《哈珀杂志》
这本小说精彩绝伦、充满智性、满怀激情,在很多方面都仿佛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这样当代作品的前兆之作。
——《奥普拉日报》
对女性友谊、自我和失去的描写感人至深。
——《柯克斯评论》
这位女权先锋写出了女性友谊的复杂性,令人耳目一新。波伏瓦在对小说的驾驭能力进一步展示了她的精湛技艺。
——《出版人周刊》
前言
在阿德里娜·德希尔教会学校,九岁的学生西蒙娜·德·波伏瓦身边坐着一位浅棕色短发的少女—伊丽莎白·拉古昂,又名扎扎,只比西蒙娜年长几天。她举止自然、风趣幽默、率真大胆,在周围的保守主义作风中显得特立独行。下学期开学时,扎扎没有来,整个世界变得黯淡无光、死气沉沉。有一天她突然来了,带来了阳光、欢乐与幸福。她聪明伶俐、多才多艺,西蒙娜被她吸引,欣赏她,为她着迷。她俩争各门功课的第一名,变得形影不离。西蒙娜在家里过得并非不幸福,她爱着自己年轻的母亲,欣赏父亲,还有个对她言听计从的妹妹,但突然发生在这个十岁小女孩身上的,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情经历:对扎扎怀有炽热的感情,崇拜她,生怕惹她不高兴。当然,西蒙娜自己还只是个脆弱的孩子,无法理解这份让她深受打击的早熟经历,而对我们这些见证者而言,她们之间的故事令人动容。和扎扎的促膝长谈在她眼中具有无穷的价值。哦!她们所受的教育给她们施加了条条框框,不能过于亲密,彼此之间以“您”相称,尽管如此,她们之间的交谈是西蒙娜跟其他人从未有过的。这份无名的情感,按照传统的说法叫作“友情”,燃烧着她崭新的心,使她惊叹,让她迷醉,这样的情感如果不是爱又会是什么呢?很快,她知道扎扎对她并没有同样的依恋之情,也并没有猜到她的感情如此热烈,但是只要能爱着,其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扎扎在她二十二岁生日前一个月骤然离世。这起意外的悲剧一直萦绕在波伏瓦心头。此后很多年,扎扎经常潜入她梦里,戴着一顶粉色遮阳帽,脸色蜡黄,以责备的眼神看着她。为了抵抗虚无和遗忘,她只能求助于文学的魔法。波伏瓦先后四次在不同题材的创作中,徒劳地尝试用文字再现扎扎,其中包括一些未出版的青年时代的小说、故事集《精神至上》(Quand prime le spirituel),以及《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中被删掉的一段。《名士风流》在一九五四年获得龚古尔奖,同年,她再一次尝试写扎扎。这次她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没有为其命名。这部作品此前没有出版过,现在是首次出版。这最后一次小说体尝试未能让她感到满意,但通过这一重要迂回,她实现了最终的文学转换:一九五八年,她将扎扎的生死往事记录在自传中,这就是《端方淑女》(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波伏瓦完成了这部小说,一直保存着它,尽管她自己对其评价比较苛刻,但这部作品有极大的价值:当面对一个谜团,疑问层出不穷时,人会变换理解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观点,做各类解释。扎扎之死有一部分便是谜团。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八年的两次创作中,关于这一死亡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首次刻画伟大友谊这一主题是在该小说中。这样令人迷惑的友谊如同爱情一般,曾让蒙田就自己与拉博埃希的关系写下:“因为是他,因为是我。”扎扎在小说中的化身是安德蕾,小说的叙述者“我”—安德蕾的朋友,叫作希尔维。无论在作品中还是生活中,“形影不离的两个人”都在一起应对各种事件,却是希尔维怀着友情将这些事情讲述出来,通过一系列对比,她的讲述揭示了这些事件无法消解的模糊性。
小说的虚构性,意味着我们需要破解书中对现实世界的一些映射和变形。书中的人物、地点、家庭情况都跟现实不同。安德蕾·卡拉尔取代现实中的伊丽莎白·拉古昂,希尔维·勒巴热替代西蒙娜·德·波伏瓦。卡拉尔家(《端方淑女》中的马比耶家)有七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男孩;拉古昂家有九个孩子,六女三男。波伏瓦只有一个妹妹,书中希尔维有两个。我们当然能认出书中的阿德莱德学校就是著名的德希尔教会学校,该校位于圣日耳曼德佩的雅各布街。正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们称两个小姑娘“形影不离”。这一表达架起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桥梁,被我们用作小说的标题。帕斯卡·布隆代尔的原型是莫里斯·梅洛—庞蒂(《端方淑女》中的普拉代儿),他幼年失怙,与母亲非常亲密,一同生活的还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跟小说中的爱玛并不相似。利穆赞大区梅里尼亚克的庄园变成了萨德纳克;而贝塔里指的是卡涅邦,波伏瓦在卡涅邦小住过两次,那是拉古昂家在朗德地区的一处庄园,还有一处在奥巴尔丹。扎扎埋在那里,在圣—邦德隆。
扎扎的死因是什么?
根据冷冰冰的科学客观性,她死于一种病毒性脑炎。但是一系列由来已久的致命因素彼此串联、交织成网,紧紧地网住了她的整个人生,最终削弱了她、耗尽了她,将她逼入绝境,让她走向疯狂和死亡。这种串联究竟是什么?波伏瓦也许会回答:“扎扎死于特立独行。”她是被谋杀而亡,她的死是一起“精神谋杀案”。
扎扎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她努力做自己,而人们想要使她相信这一企图是罪恶的。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生于一个激进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在这样一个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家庭,女孩子必须自我忘却、自我放弃、学会适应。
因为扎扎与众不同,她无法“学会适应”—这个阴森的词语意味着要将自己嵌入预制的模具中,模具里有一个为您准备的空格,和其他空格挨在一起。但凡超出空格的部分都会被抑制、碾压,如同废料一般被丢弃。扎扎无法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人们就压抑了她的独特性。罪行、谋杀正在于此。波伏瓦憎恶地回想起在卡涅邦拍的一张家庭合照:六个女孩穿着同样的蓝色塔夫绸连衣裙,头上清一色地戴着矢车菊装点的草帽。扎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永远属于她的位置:拉古昂家的二女儿。年轻的波伏瓦强烈抗拒这张照片。不,扎扎不是那样的,她是“独一无二的”。不期而至的自由,是她家任何一条家规所不认可的。那群人不懈地围困她,她成了“社会义务”的猎物。她身边总是有自家或堂表亲家的兄弟姐妹、她的朋友们,还有各类近亲远戚,她需要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忙碌,参与社交活动,接待访客,参加集体娱乐,没有片刻能自由支配。家里人从来不让她一个人待着,也不让她单独跟密友相会,她不属于她自己,没有私人时间,就连拉小提琴和学习的时间都没有。孤独这项特权她无法享有。因此,贝塔里的夏季于她而言简直是一座地狱。她感到窒息,他人无所不在—这让人联想到某些修会里相似的苦修,她那么想要逃离这种环境,竟至于用斧头砍伤自己的脚,以此来逃避一项可恨的苦差。在她家所属的阶层,女孩子不应该特立独行,不可以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他人而活。“妈妈从没有任何事是为了她自己而做的,她一生都在奉献自我。”有一天她这样说道。在这些使人异化的传统的不断浸润下,一切活生生的个性化发展都被遏制在萌芽状态。然而对于波伏瓦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丑陋行径,这也正是小说意欲揭露之物:一个可说是哲学性的丑陋行径。之所以说是哲学性的,是因为它侵害了人的境遇。肯定主体性的绝对价值,这是波伏瓦思想和作品的核心,并非个体—某一号样品—的价值,而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纪德所言“最无可取代的存在”,成为在此时此地就具有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去爱昙花一现的事物。”哲学思考也为这种不可动摇的基本信念提供支持:“绝对(l’absolu)”是在人间、在世上、在我们唯一和独一无二的存在中发生的。因此,我们知道扎扎的故事有着重要意义。
这起悲剧的推动力有哪些?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其中一些显而易见:她爱着母亲,一旦遭到母亲反对就感到左右为难。扎扎对母亲的爱是热烈的、充满嫉妒的、不幸的爱。她如此冲动地爱着母亲,母亲对她却有几分冷淡,作为二女儿,她感到被淹没在兄弟姐妹群里,只是母亲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拉古昂夫人手法高明,她没有用个人权威来管束孩子们的调皮玩闹,所以当涉及重大事务时,由于她的权威丝毫没有受损,就能更好地控制他们。一个女孩子要么嫁人,要么进修道院,无法根据个人性情、爱好来决定自身命运。安排婚姻的是家庭,通过组织“相亲”,根据价值观、宗教、社会等级、经济状况等标准来挑选合适的对象。这个阶层的人结婚讲究门当户对。在扎扎十五岁时,她第一次遭遇了这些致命的教条:家人突然阻止她跟堂兄贝尔纳见面,斩断了她对他的爱。第二次是在二十岁那年,她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她选择了不被看好的帕斯卡·布隆代尔,想要嫁给他,在那群人眼中,这是不可接受的。扎扎的悲剧在于,在她内心最深处,一个同盟暗地里支持了敌人:她没有勇气反抗一个神圣且心爱的权威,于是死于该权威对她的制裁。即使母亲的责备侵蚀了她的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她也接受了这些责备,甚至要为给她判刑的法官辩护。拉古昂夫人的保守主义犹如一块顽石,但这块顽石仿佛有一丝裂缝:年轻时似乎她也被她母亲强制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这就使得她对女儿的压制更加不通情理。她不得不“学会适应”—这个残酷的词应运而生—自我否定。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大权在握,她决定如法炮制,也去粉碎女儿的个性。在她那副镇定自若的面孔下,隐藏着怎样的沮丧和愤恨?
虔诚,或者说唯灵论,像沉重的盖子盖住了扎扎的生活。她沉浸在充斥着宗教气氛的生活环境里:出身于一个激进的天主教徒世家,父亲担任“多子女家庭联合会”会长,母亲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区享有声望,一位兄长做了神父,一位姐姐进了修道院。每年全家人都要参加卢尔德朝圣。波伏瓦所揭露的“唯灵论”,是“纯洁的白色”,是用超自然光晕掩盖极为世俗的阶级价值。当然,欺骗他人者先被欺骗。一切自动归于宗教,一切都变得合理。“我们只是上帝手里的工具。”卡拉尔先生在女儿死后这样说。扎扎之所以屈从,是因为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天主教,而对一般人而言,天主教只是一种方便的、流于形式的实践罢了。她独特的品质又一次伤害了她自己。尽管已经识破她那个阶层“道德主义者”的虚伪、欺骗和自私,了解他们利欲熏心、锱铢必较,跟福音书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她的信仰除了有过短暂的动摇外,一直保持到底。然而,内心的流放、亲人的不理解、与一种存在主义式孤独绝缘—家人从不让她独自待着,这些都让她痛苦不已。
她在精神世界的严肃与真诚却只换来对自己的侮辱与折磨,将自己逼入内心矛盾的绝境。因为跟很多人不一样,对她而言,信仰不是一种讨人欢心的上帝的工具,也不是为自己寻找理由、进行自我辩护、逃避责任的手段,而是对沉默、晦暗、隐而不显的上帝痛苦的质疑。她折磨着自己,内心撕裂:应该按照母亲的叮嘱,听话、变愚钝、服从、忘却自我,还是应该像朋友鼓励的那样,不服从、反抗,充分发挥上天赐予自己的天赋与才能?上帝的意志是怎样的?上帝对她的期许是什么?
萦绕不去的罪的念头侵蚀了她的生命力。与她的朋友希尔维不同,安德蕾/扎扎对性事比较了解。在她十五岁那年,卡拉尔夫人几乎是以一种虐待狂似的粗暴,直白露骨地告诉她婚姻的真相。提及新婚之夜,她毫无掩饰地说:“这是一个要去经历的糟糕时刻。”扎扎的自身经验却与这种粗暴的描绘大不相同:她了解性的魔力,体验过那种意乱情迷,她跟男朋友贝尔纳的吻不是柏拉图式的吻。她嘲笑身边那些年轻处女的愚蠢,嘲笑正统派人士的虚伪,那些人“漂白”、否认或掩饰活生生的肉体涌现的欲望。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她知道自己面对诱惑没有抵抗力,她灼热的感性、激烈的性情、对生活的肉欲之爱都被重重顾虑所败坏:即使在最细微的欲望中,她都怀疑存在着罪,肉体之罪。悔恨、恐惧、负罪感让她心神不宁,对自我的谴责加重了她对弃世的向往,强化了她对虚无的欲望和其他令人不安的自毁倾向。她最终在母亲和帕斯卡面前让步了,两个人都试图让她相信长时间处在订婚状态是危险的,她同意远走英国,但其实内心十分抗拒。最后这一次对她的残酷逼迫加速了灾难的到来。扎扎死于所有这些让她内心分裂的矛盾力量。
在这部小说里,希尔维的角色是朋友,所起的作用仅仅是让人理解安德蕾。正如学者爱莉安娜·勒卡姆—达波纳(Eliane Lecarme-Tabone)所强调的那样,希尔维自身的回忆极少出现,关于她自己的生活、个人抗争、解放自我的动荡经历我们一无所知,尤其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之间的根本对立—《端方淑女》的核心主题—在这里只是稍微提及。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出她在安德蕾的阶层不受待见,几乎不被接受。卡拉尔一家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希尔维自己家本来属于不错的中产阶级,“一战”之后破产了,社会地位下降。她在贝塔里小住的时候,时常蒙受悄无声息的侮辱:她的发型、服饰被人指指点点。安德蕾悄悄在她房间的衣橱里挂了一条漂亮裙子。还有更严重的:卡拉尔夫人不信任她,觉得她误入歧途—她这样一位在索邦学习的年轻姑娘,将来要从事一份职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取得独立。那一晚在厨房里,希尔维向扎扎吐露心声,直言从前扎扎于自己而言意味着整个世界,扎扎大吃一惊,这让人心碎的一幕标志着两位朋友的关系扭转方向了。从此以后,是扎扎更爱对方。在希尔维面前,无尽的世界向她敞开,而安德蕾走向死亡。不过,是希尔维/西蒙娜复活了安德蕾。怀着温柔与敬重,她借助文学的力量重现了安德蕾的生命,肯定了她的存在价值。我还想提醒,《端方淑女》四个部分结尾词分别为:“扎扎”“讲述”“死亡”“她的死亡”。波伏瓦有负罪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继续活着是一种过错。扎扎是她逃离而付出的代价;她甚至在未出版的笔记中写下“祭品”这个词,扎扎是她获取自由而献出的祭品。但对我们而言,她的小说难道没有完成她赋予文字的近乎神圣的使命:抵抗时间,抵抗遗忘,抵抗死亡,“承认瞬间(l’instant)的绝对在场,一瞬即永恒”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扎扎在她二十二岁生日前一个月骤然离世。这起意外的悲剧一直萦绕在波伏瓦心头。此后很多年,扎扎经常潜入她梦里,戴着一顶粉色遮阳帽,脸色蜡黄,以责备的眼神看着她。为了抵抗虚无和遗忘,她只能求助于文学的魔法。波伏瓦先后四次在不同题材的创作中,徒劳地尝试用文字再现扎扎,其中包括一些未出版的青年时代的小说、故事集《精神至上》(Quand prime le spirituel),以及《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中被删掉的一段。《名士风流》在一九五四年获得龚古尔奖,同年,她再一次尝试写扎扎。这次她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没有为其命名。这部作品此前没有出版过,现在是首次出版。这最后一次小说体尝试未能让她感到满意,但通过这一重要迂回,她实现了最终的文学转换:一九五八年,她将扎扎的生死往事记录在自传中,这就是《端方淑女》(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波伏瓦完成了这部小说,一直保存着它,尽管她自己对其评价比较苛刻,但这部作品有极大的价值:当面对一个谜团,疑问层出不穷时,人会变换理解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观点,做各类解释。扎扎之死有一部分便是谜团。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八年的两次创作中,关于这一死亡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首次刻画伟大友谊这一主题是在该小说中。这样令人迷惑的友谊如同爱情一般,曾让蒙田就自己与拉博埃希的关系写下:“因为是他,因为是我。”扎扎在小说中的化身是安德蕾,小说的叙述者“我”—安德蕾的朋友,叫作希尔维。无论在作品中还是生活中,“形影不离的两个人”都在一起应对各种事件,却是希尔维怀着友情将这些事情讲述出来,通过一系列对比,她的讲述揭示了这些事件无法消解的模糊性。
小说的虚构性,意味着我们需要破解书中对现实世界的一些映射和变形。书中的人物、地点、家庭情况都跟现实不同。安德蕾·卡拉尔取代现实中的伊丽莎白·拉古昂,希尔维·勒巴热替代西蒙娜·德·波伏瓦。卡拉尔家(《端方淑女》中的马比耶家)有七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男孩;拉古昂家有九个孩子,六女三男。波伏瓦只有一个妹妹,书中希尔维有两个。我们当然能认出书中的阿德莱德学校就是著名的德希尔教会学校,该校位于圣日耳曼德佩的雅各布街。正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们称两个小姑娘“形影不离”。这一表达架起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桥梁,被我们用作小说的标题。帕斯卡·布隆代尔的原型是莫里斯·梅洛—庞蒂(《端方淑女》中的普拉代儿),他幼年失怙,与母亲非常亲密,一同生活的还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跟小说中的爱玛并不相似。利穆赞大区梅里尼亚克的庄园变成了萨德纳克;而贝塔里指的是卡涅邦,波伏瓦在卡涅邦小住过两次,那是拉古昂家在朗德地区的一处庄园,还有一处在奥巴尔丹。扎扎埋在那里,在圣—邦德隆。
扎扎的死因是什么?
根据冷冰冰的科学客观性,她死于一种病毒性脑炎。但是一系列由来已久的致命因素彼此串联、交织成网,紧紧地网住了她的整个人生,最终削弱了她、耗尽了她,将她逼入绝境,让她走向疯狂和死亡。这种串联究竟是什么?波伏瓦也许会回答:“扎扎死于特立独行。”她是被谋杀而亡,她的死是一起“精神谋杀案”。
扎扎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她努力做自己,而人们想要使她相信这一企图是罪恶的。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生于一个激进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在这样一个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家庭,女孩子必须自我忘却、自我放弃、学会适应。
因为扎扎与众不同,她无法“学会适应”—这个阴森的词语意味着要将自己嵌入预制的模具中,模具里有一个为您准备的空格,和其他空格挨在一起。但凡超出空格的部分都会被抑制、碾压,如同废料一般被丢弃。扎扎无法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人们就压抑了她的独特性。罪行、谋杀正在于此。波伏瓦憎恶地回想起在卡涅邦拍的一张家庭合照:六个女孩穿着同样的蓝色塔夫绸连衣裙,头上清一色地戴着矢车菊装点的草帽。扎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永远属于她的位置:拉古昂家的二女儿。年轻的波伏瓦强烈抗拒这张照片。不,扎扎不是那样的,她是“独一无二的”。不期而至的自由,是她家任何一条家规所不认可的。那群人不懈地围困她,她成了“社会义务”的猎物。她身边总是有自家或堂表亲家的兄弟姐妹、她的朋友们,还有各类近亲远戚,她需要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忙碌,参与社交活动,接待访客,参加集体娱乐,没有片刻能自由支配。家里人从来不让她一个人待着,也不让她单独跟密友相会,她不属于她自己,没有私人时间,就连拉小提琴和学习的时间都没有。孤独这项特权她无法享有。因此,贝塔里的夏季于她而言简直是一座地狱。她感到窒息,他人无所不在—这让人联想到某些修会里相似的苦修,她那么想要逃离这种环境,竟至于用斧头砍伤自己的脚,以此来逃避一项可恨的苦差。在她家所属的阶层,女孩子不应该特立独行,不可以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他人而活。“妈妈从没有任何事是为了她自己而做的,她一生都在奉献自我。”有一天她这样说道。在这些使人异化的传统的不断浸润下,一切活生生的个性化发展都被遏制在萌芽状态。然而对于波伏瓦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丑陋行径,这也正是小说意欲揭露之物:一个可说是哲学性的丑陋行径。之所以说是哲学性的,是因为它侵害了人的境遇。肯定主体性的绝对价值,这是波伏瓦思想和作品的核心,并非个体—某一号样品—的价值,而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纪德所言“最无可取代的存在”,成为在此时此地就具有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去爱昙花一现的事物。”哲学思考也为这种不可动摇的基本信念提供支持:“绝对(l’absolu)”是在人间、在世上、在我们唯一和独一无二的存在中发生的。因此,我们知道扎扎的故事有着重要意义。
这起悲剧的推动力有哪些?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其中一些显而易见:她爱着母亲,一旦遭到母亲反对就感到左右为难。扎扎对母亲的爱是热烈的、充满嫉妒的、不幸的爱。她如此冲动地爱着母亲,母亲对她却有几分冷淡,作为二女儿,她感到被淹没在兄弟姐妹群里,只是母亲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拉古昂夫人手法高明,她没有用个人权威来管束孩子们的调皮玩闹,所以当涉及重大事务时,由于她的权威丝毫没有受损,就能更好地控制他们。一个女孩子要么嫁人,要么进修道院,无法根据个人性情、爱好来决定自身命运。安排婚姻的是家庭,通过组织“相亲”,根据价值观、宗教、社会等级、经济状况等标准来挑选合适的对象。这个阶层的人结婚讲究门当户对。在扎扎十五岁时,她第一次遭遇了这些致命的教条:家人突然阻止她跟堂兄贝尔纳见面,斩断了她对他的爱。第二次是在二十岁那年,她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她选择了不被看好的帕斯卡·布隆代尔,想要嫁给他,在那群人眼中,这是不可接受的。扎扎的悲剧在于,在她内心最深处,一个同盟暗地里支持了敌人:她没有勇气反抗一个神圣且心爱的权威,于是死于该权威对她的制裁。即使母亲的责备侵蚀了她的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她也接受了这些责备,甚至要为给她判刑的法官辩护。拉古昂夫人的保守主义犹如一块顽石,但这块顽石仿佛有一丝裂缝:年轻时似乎她也被她母亲强制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这就使得她对女儿的压制更加不通情理。她不得不“学会适应”—这个残酷的词应运而生—自我否定。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大权在握,她决定如法炮制,也去粉碎女儿的个性。在她那副镇定自若的面孔下,隐藏着怎样的沮丧和愤恨?
虔诚,或者说唯灵论,像沉重的盖子盖住了扎扎的生活。她沉浸在充斥着宗教气氛的生活环境里:出身于一个激进的天主教徒世家,父亲担任“多子女家庭联合会”会长,母亲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区享有声望,一位兄长做了神父,一位姐姐进了修道院。每年全家人都要参加卢尔德朝圣。波伏瓦所揭露的“唯灵论”,是“纯洁的白色”,是用超自然光晕掩盖极为世俗的阶级价值。当然,欺骗他人者先被欺骗。一切自动归于宗教,一切都变得合理。“我们只是上帝手里的工具。”卡拉尔先生在女儿死后这样说。扎扎之所以屈从,是因为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天主教,而对一般人而言,天主教只是一种方便的、流于形式的实践罢了。她独特的品质又一次伤害了她自己。尽管已经识破她那个阶层“道德主义者”的虚伪、欺骗和自私,了解他们利欲熏心、锱铢必较,跟福音书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她的信仰除了有过短暂的动摇外,一直保持到底。然而,内心的流放、亲人的不理解、与一种存在主义式孤独绝缘—家人从不让她独自待着,这些都让她痛苦不已。
她在精神世界的严肃与真诚却只换来对自己的侮辱与折磨,将自己逼入内心矛盾的绝境。因为跟很多人不一样,对她而言,信仰不是一种讨人欢心的上帝的工具,也不是为自己寻找理由、进行自我辩护、逃避责任的手段,而是对沉默、晦暗、隐而不显的上帝痛苦的质疑。她折磨着自己,内心撕裂:应该按照母亲的叮嘱,听话、变愚钝、服从、忘却自我,还是应该像朋友鼓励的那样,不服从、反抗,充分发挥上天赐予自己的天赋与才能?上帝的意志是怎样的?上帝对她的期许是什么?
萦绕不去的罪的念头侵蚀了她的生命力。与她的朋友希尔维不同,安德蕾/扎扎对性事比较了解。在她十五岁那年,卡拉尔夫人几乎是以一种虐待狂似的粗暴,直白露骨地告诉她婚姻的真相。提及新婚之夜,她毫无掩饰地说:“这是一个要去经历的糟糕时刻。”扎扎的自身经验却与这种粗暴的描绘大不相同:她了解性的魔力,体验过那种意乱情迷,她跟男朋友贝尔纳的吻不是柏拉图式的吻。她嘲笑身边那些年轻处女的愚蠢,嘲笑正统派人士的虚伪,那些人“漂白”、否认或掩饰活生生的肉体涌现的欲望。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她知道自己面对诱惑没有抵抗力,她灼热的感性、激烈的性情、对生活的肉欲之爱都被重重顾虑所败坏:即使在最细微的欲望中,她都怀疑存在着罪,肉体之罪。悔恨、恐惧、负罪感让她心神不宁,对自我的谴责加重了她对弃世的向往,强化了她对虚无的欲望和其他令人不安的自毁倾向。她最终在母亲和帕斯卡面前让步了,两个人都试图让她相信长时间处在订婚状态是危险的,她同意远走英国,但其实内心十分抗拒。最后这一次对她的残酷逼迫加速了灾难的到来。扎扎死于所有这些让她内心分裂的矛盾力量。
在这部小说里,希尔维的角色是朋友,所起的作用仅仅是让人理解安德蕾。正如学者爱莉安娜·勒卡姆—达波纳(Eliane Lecarme-Tabone)所强调的那样,希尔维自身的回忆极少出现,关于她自己的生活、个人抗争、解放自我的动荡经历我们一无所知,尤其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之间的根本对立—《端方淑女》的核心主题—在这里只是稍微提及。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出她在安德蕾的阶层不受待见,几乎不被接受。卡拉尔一家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希尔维自己家本来属于不错的中产阶级,“一战”之后破产了,社会地位下降。她在贝塔里小住的时候,时常蒙受悄无声息的侮辱:她的发型、服饰被人指指点点。安德蕾悄悄在她房间的衣橱里挂了一条漂亮裙子。还有更严重的:卡拉尔夫人不信任她,觉得她误入歧途—她这样一位在索邦学习的年轻姑娘,将来要从事一份职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取得独立。那一晚在厨房里,希尔维向扎扎吐露心声,直言从前扎扎于自己而言意味着整个世界,扎扎大吃一惊,这让人心碎的一幕标志着两位朋友的关系扭转方向了。从此以后,是扎扎更爱对方。在希尔维面前,无尽的世界向她敞开,而安德蕾走向死亡。不过,是希尔维/西蒙娜复活了安德蕾。怀着温柔与敬重,她借助文学的力量重现了安德蕾的生命,肯定了她的存在价值。我还想提醒,《端方淑女》四个部分结尾词分别为:“扎扎”“讲述”“死亡”“她的死亡”。波伏瓦有负罪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继续活着是一种过错。扎扎是她逃离而付出的代价;她甚至在未出版的笔记中写下“祭品”这个词,扎扎是她获取自由而献出的祭品。但对我们而言,她的小说难道没有完成她赋予文字的近乎神圣的使命:抵抗时间,抵抗遗忘,抵抗死亡,“承认瞬间(l’instant)的绝对在场,一瞬即永恒”吗?
精彩书摘
“班上最好的学生就是您吗?”
“我叫希尔维·勒巴热,”我说,“您呢?”
“安德蕾·卡拉尔,今年九岁。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小?我之前被烧伤过,耽误了长个儿。有一整年我都没有学习,妈妈想让我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您能把去年的课堂笔记借我吗?”
“可以的。”我说。
安德蕾说话时显得成熟稳重,语速很快,毫不含混,这让我感到几分惊讶。她以一种将信将疑的目光打量着我。
“旁边的同学告诉我,您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她边说边侧头看了一眼丽赛特,“这是真的吗?”
“我也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我谦虚地回答。
“我叫希尔维·勒巴热,”我说,“您呢?”
“安德蕾·卡拉尔,今年九岁。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小?我之前被烧伤过,耽误了长个儿。有一整年我都没有学习,妈妈想让我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您能把去年的课堂笔记借我吗?”
“可以的。”我说。
安德蕾说话时显得成熟稳重,语速很快,毫不含混,这让我感到几分惊讶。她以一种将信将疑的目光打量着我。
“旁边的同学告诉我,您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她边说边侧头看了一眼丽赛特,“这是真的吗?”
“我也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我谦虚地回答。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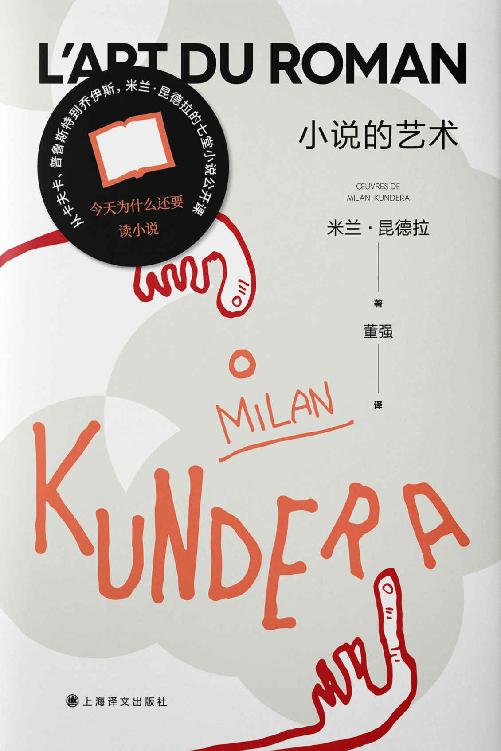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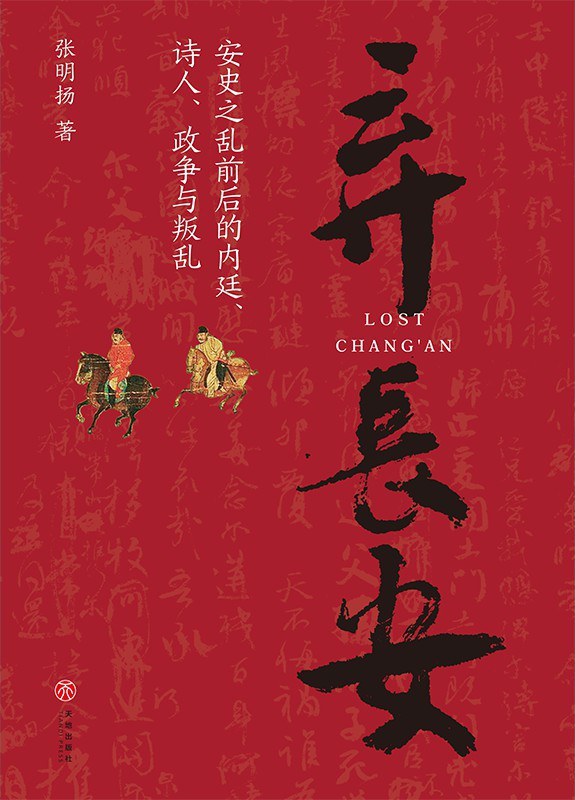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