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政策制定为何重富轻贫?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只对富人的偏好做出反应,那么这个国家还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吗?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应该对政府政策有平等的影响,但正如本书所展示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只对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的偏好做出反应。本书以敏锐的分析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审视了数以千计的政策改革提案,以及穷人、中产阶层和富裕的美国人对每项政策的支持程度。本书的发现是惊人的:当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偏好与富人的偏好不一致时,政策结果与处境较差的群体的愿望之间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富裕的美国人的偏好与政策结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书还表明,这种代表性的不平等广泛分布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和时间段,并且受到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的影响。
编辑推荐
本书荣获2016年美国民意研究协会图书奖
美国政治学会2013年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奖
美国政治学会2013年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奖
目录
作者简介
导论
本书计划
第一章 公民能力和民主决策制定
民主是什么?
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
美国大众是否持有有意义的政策偏好?
寻求提示作为政治偏好的基础
议题大众
“加总的魔力”和大众偏好的质量
错误的感觉(意识)和精英操纵
信息获取和加总效果有多好?
问题措辞和框架效应
虚假态度和虚假的无态度
偏好强度与民主回应性
外显的和潜在的偏好
民主:政府的最差形式……
评估政策回应性
政策回应性的替代性测量
民主和代表性
第二章 数据与方法
界定合适的政策偏好集
政策偏好与调查日程
数据库
政策结果编码
利用收入和教育来插补偏好
偏好和结果测量的信度(可靠性、准确度)
评估回应性:一致性与影响
第三章 偏好—政策关联
政策回应性的标准化模型
政策回应性的经验证据
不同收入群体间偏好有差异时的政策回应性
估计收入群体的政策影响力的其他方法
对偏好和政策结果关联的解释
第四章 政策领域与民主回应性
对外政策、防卫(国防)和恐怖主义
宗教价值观议题
经济政策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政策与代表性不平等
第五章 利益集团与民主回应性
利益集团结盟与大众政策偏好
利益集团联盟测量
利益集团联盟的分布
利益集团联盟和政策结果
利益集团作为遗漏变量
利益集团参与和政策回应性
利益集团和大众偏好作为力量倍增器
不同议题领域的利益集团联盟和大众偏好
不同议题领域的利益集团、大众和政策结果
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利益集团联盟与具体的政策结果
个体利益集团和大众政策偏好
第六章 政党、选举与民主回应性
拓展和重构偏好/政策数据库
强制回应性与选举周期
下降的回应性与党派政权时长
党派控制
小结
第七章 不同时期的民主回应性
政治环境变动
政策回应性随时间的增长
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动
极化和僵局
多数党席位优势与国会控制的不确定性
变化的情况和变化的回应性
约翰逊政府时期政策回应性的缺乏
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的回应性
对乔治·W.布什税收削减政策的大众支持
小结
第八章 金钱与美国政治
百万富翁俱乐部
收入和政治参与
一般富裕和真富
金钱与政治结果
竞选资金改革
提高民主回应性
附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东方编译所译丛·政治科学
导论
本书计划
第一章 公民能力和民主决策制定
民主是什么?
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
美国大众是否持有有意义的政策偏好?
寻求提示作为政治偏好的基础
议题大众
“加总的魔力”和大众偏好的质量
错误的感觉(意识)和精英操纵
信息获取和加总效果有多好?
问题措辞和框架效应
虚假态度和虚假的无态度
偏好强度与民主回应性
外显的和潜在的偏好
民主:政府的最差形式……
评估政策回应性
政策回应性的替代性测量
民主和代表性
第二章 数据与方法
界定合适的政策偏好集
政策偏好与调查日程
数据库
政策结果编码
利用收入和教育来插补偏好
偏好和结果测量的信度(可靠性、准确度)
评估回应性:一致性与影响
第三章 偏好—政策关联
政策回应性的标准化模型
政策回应性的经验证据
不同收入群体间偏好有差异时的政策回应性
估计收入群体的政策影响力的其他方法
对偏好和政策结果关联的解释
第四章 政策领域与民主回应性
对外政策、防卫(国防)和恐怖主义
宗教价值观议题
经济政策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政策与代表性不平等
第五章 利益集团与民主回应性
利益集团结盟与大众政策偏好
利益集团联盟测量
利益集团联盟的分布
利益集团联盟和政策结果
利益集团作为遗漏变量
利益集团参与和政策回应性
利益集团和大众偏好作为力量倍增器
不同议题领域的利益集团联盟和大众偏好
不同议题领域的利益集团、大众和政策结果
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利益集团联盟与具体的政策结果
个体利益集团和大众政策偏好
第六章 政党、选举与民主回应性
拓展和重构偏好/政策数据库
强制回应性与选举周期
下降的回应性与党派政权时长
党派控制
小结
第七章 不同时期的民主回应性
政治环境变动
政策回应性随时间的增长
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动
极化和僵局
多数党席位优势与国会控制的不确定性
变化的情况和变化的回应性
约翰逊政府时期政策回应性的缺乏
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的回应性
对乔治·W.布什税收削减政策的大众支持
小结
第八章 金钱与美国政治
百万富翁俱乐部
收入和政治参与
一般富裕和真富
金钱与政治结果
竞选资金改革
提高民主回应性
附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东方编译所译丛·政治科学
前言
导论
几十年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写道:“在这个国家,我们要么实现民主,要么让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被称为“新镀金时代”。美国的财富事实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比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严重。在这本书中,我考察了美国个体的财富资源与他们的政治权力的关系,试图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现代美国印证了布兰代斯大法官的断言。
每个社会的公民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但是民主社会一般被认为能够容纳相当程度的政治平等,即便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在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公式中,民主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是“视政府对其公民偏好的持续回应为政治平等的表现”。这个政治平等的理念在经济不平等面前或许不可能完全实现——在每个民主国家,拥有更多资源的公民更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但是一个社会中政治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加剧或减轻它的条件,能够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许多的民主质量信息。
我在本书的目标是通过考察由美国公众所表达的政策偏好与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者所采用的政策之间的关系,来展示和解释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代表性的不同模式。为此,我收集了一个反映美国不同收入阶层政策偏好的调查数据库。这些数据反映了成百上千的受访者对政府各种政策的回答——从提高最低工资到限制堕胎,再到美国向波斯尼亚派军。在随后的章节,我通过比较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对特定国家政策变动的诉求与由总统和国会决定的实际政策进程来分析这些数据。而我的发现很难与达尔民主公式中的政治平等概念相符合。美国政府确实对公众的偏好进行了回应,但这种回应强烈倾向于最富裕的公民群体。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似乎并未对政府采取或未采取的政策有什么本质的影响。
正如我要在后面所讲的那样,代表性不平等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环境及不同政策领域下广泛存在。然而也有例外,也有更倒向于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代表性。在识别这些情形时,我不仅想表明美国代表性不平等的变化,还想找出提高政府政策制定者在全体美国人民中的回应的平等性的更好方法。
本书计划
我首先要强调民主国家中大众意见所扮演的角色。许多观察者把调查受访者表达的政策偏好很大程度上视为消息不灵通的“无态度”(nonattitudes)。在公众对大众事务了解度和参与度低的情况下,我询问了大众政策偏好是否值得左右政府政策。第一章通过对公共舆论学者提出的“大众无知论”(public ignorance)的讨论来开始这个问题。我认为尽管大众很难达到许多观察者对公民知识和参与度的标准,但美国人在大众观点调查中所表达的政策偏好——作为美国评判民主回应性程度的一个标准,在事实上应该得到尊重。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该总是遵从多数意见,但它确实意味着大众政策与公众偏好的实质性偏差是民主治理失败的初步指标,并且政策制定者对优势群体偏好回应的不平等也是违背民主平等规则的一个基本指标。
第二章描述了我研究民主代表性的方法。我首先考虑了识别一系列现实和潜在的既不太泛(如哪些美国人拥有有意义的观点这样次要且模糊的议题)也不太窄(如政治行动者没有被纳入政府议程中)的议题的困难。随后我描述了调查数据和政策结果编码,这些是我的研究的基础。最后,第二章还强调了评估政府对公众回应性的替代性方法的优劣势。我还特别指出了使用现实政策而非国会投票作为利益结果(outcome of interests)的好处。首先,考察国会唱名表决(代表性分析中的常用方法)不能将政府议程设置权的重要性纳入其中,议程设置权决定了在众多潜在议题中选择或忽略哪个。其次,许多国会唱名表决议题的关键政策决定是在立法过程之前闭门决定的。最后,我还指出要理解代表性不平等,需要对离散的政策决定而不是宽泛的对自由或保守倾向的分析。富裕的美国人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保守,而在诸如堕胎、同性恋权利以及外国援助等问题上更自由化。相应的,当这些相反的议题都纳入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指标时,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偏好差异就会被抵消。
在第三章,我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评估了公众偏好和政府政策的关联。我发现了政策结果和富裕群体之间存在着相当强的关联,与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则有更弱的关联。我还发现政策结果与后者偏好的关联大部分还是基于后者与前者有共同的偏好。当不那么富裕的美国群体持有与富裕群体不同的偏好时,政策对富裕群体的回应仍然很强,但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几乎为零。
我对政策回应性的考察还表明,偏好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在高度支持或者反对政策变动上是最明显的。比如,如果意见是较为平均地分配的话,20%以内的差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比如40%与60%的支持率之间的差别),而更大的差异,比如意见一边倒(如20%—40%或60%—80%的支持率)时则会有更大的影响。这种规律意味着公众偏好的政治意义更多的在于相关群体支持或反对的“程度”上,而不是简单的多数支持或反对的“差异”上。
第三章也强调了我发现的代表性不平等的替代解释。首先,我展示了我的政策偏好的测量信度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异不大,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导致的差异也如此(比如我的数据库中对某一问题有观点的不同收入群体受访者比例)。其次,观点强度的差异(比如在多大程度上受访者的偏好是“非常”或者“有点”)也不能解释代表性不平等的差异规律。最后,我强调了偏好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联不仅反映了大众(或者说是大众的富裕部分)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还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精英对大众偏好的影响的可能性。根据从我的数据库中得出的诸多证明和对前人的研究,我指出尽管这些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观察偏好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联,大众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更能解释我在分析中所观察到的关联。
第三章表明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间存在着大量的代表性不平等,而第四章则观察了这种不平等在实质性议题领域内的分布。我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我所检验的四个议题领域内的不平等回应性的整体模式是相似的。对每个政策领域偏好与政策结果的仔细观察,表明了如果政府能够平等地反映全体美国人的偏好的话,政府政策会如何变化。比如,在经济领域,我们会期望有一个更累进的税收体系、更严格的公司管制和更高的最低工资;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更具保护性的贸易体制和更少的国外援助;在涉及宗教或道德问题的政策上,比如堕胎和同性恋权利,则会更加保守。在这些政策上,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是大多数支持哪边的问题。然而像第三章所表明的那样,支持程度(或反对程度)只是政治性的间接影响,取决于是否大多数支持或反对这个政策。
我在第四章的分析展示了一个社会福利案例,是一个对代表性不平等一般模式的局部的例外。在社会安全问题、医疗、教育券以及市政工程支出上,政策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偏好回应度要高于我考察的其他议题领域。我指出原因在于穷人和中产阶层美国人在这些议题上有利益集团同盟,在其他领域则没有这样的同盟。美国退休工人协会(AARP)、教师联盟、卫生行业以及其他游说团体在这些问题上与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群体偏好一致,并且致力于将政策结果向非优势群体和利益集团更希望的方向推动。
第四章中利益集团的识别对于解释代表性不平等同等重要,这引起了第五章对利益集团角色的更广泛的考察。针对数据库中的每个政策变动,我开发了一个利益集团结盟指数(measure of interest-group alignment)来做这些分析。利用这个指数,我发现当利益集团联盟与政策结果强烈相关时,它们并不能解释先前章节里所展示的代表性不平等。而当利益集团更多地参与到某一议题时,大众偏好(或者说大众中的富裕群体)或多或少有影响,但也并不能解释(代表性不平等)。相反,我认为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影响政府政策的基本平行的渠道。当利益集团和富裕群体达成一致时,政策制定者很可能服从这个诉求。而当这两者的目的不一致时,他们会一贯地阻止政策变化——不管是利益集团还是支持维持现状的富裕群体。我总结如下:利益集团有助于解释我的数据库中政策结果模式,并能解释那些反常的案例,如那些与穷人或中产阶层而非富裕群体的偏好更一致的情况。但是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对政策回应性中的贫富偏差做出解释。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我考察了政治条件(political conditions)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政策回应性的影响。第六章从对数据库增加和结构修改部分的描述开始,来更好地评估代表性是如何随着时间和政治背景的变化而不同。随后我考察了选举周期的角色,表明对所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在总统选举年都是最高的,且最不富裕群体的“代表性激增”最大。相应的,代表性不平等在总统选举年是最低的(即便是在这些时期,富裕人群的偏好与政策仍保持着最强的关联,而低收入人群的偏好与政策关联最弱)。我也在第六章表明,对富裕群体的偏好回应性在总统控制权在政党之间转移后的第一年会增加。这个模式对中产阶层的效力要弱得多,而对穷人则完全行不通。因此,这种政策制定的波动——典型地刻画了华盛顿的新政党政权特征——倾向于迎合富裕群体而非其他人的偏好。
最后,通过对共和党控制国会和总统时期与民主党主导联邦政府时期的比较,第六章探讨了政党对代表性的影响。民主党长期被视为工薪阶层政党,相较于富裕群体,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也一贯被更多地视为民主党支持者。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民主党执政时,代表性不平等更大,对所有收入阶层(包括穷人)的回应性更低。对那些解释政党代表性模式的特定问题的分析表明,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两党核心政策承诺的后果,这些承诺包括不受大众欢迎的增税(和受欢迎的减税)、批准里根国防建设法案、支持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至少在它们早期的时候),反对放松移民管制,以及支持乔治·W.布什的“基于信仰的行动”。除此之外,民主党与有组织的劳工的长期联盟也随着该党在过去几十年中采取了对管制和贸易政策更市场化的政策走向而受到侵蚀(例如民主党执政下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在社会福利领域,一个不同的政党模式也产生了,但却是一个民主党执政对穷人回应性更高和共和党执政对富人回应性更高的情况(对中产阶层的政策回应性在两党之间差不多)。
值得强调的是,共和党执政比民主党执政对穷人更强的政策回应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物质上更有利于穷人的政策更有可能在共和党掌握权力时被采用。我在第六章表明,有着明显的倾向底层再分配作用的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更有可能被采用,而那些具有倾向高层的再分配作用的政策,比如减少房产税,在共和党执政时更常见。但这些再分配政策,尽管很重要,仅仅是我的数据库中政策的一小部分,而且对这些政策的偏好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持久和强烈。
第七章强调了过去几十年间更加广泛的政策回应性趋势。我曾预期代表性不平等在美国是随着经济不平等而增长的。我也确实在我涵盖了过去40年的数据库中,发现了这种对富裕群体而不是其他收入群体回应性稳定增加的证据。但是故事远比这复杂,而且短期的政治条件波动对掩盖长期趋势以及形成对所有收入群体回应性有着重要影响。第七章特别展示了一个席位平均分配的国会,它一视同仁地提升对穷人、中产阶层、富裕群体的回应性,而政党和政治家却(暂时地)忽略了他们在获取大众支持时所做的承诺。我还表明政党极化导致的政策僵局还会出人意料地提升回应性。这种僵局会减少政策变动,并且相应地降低了联邦政府重视公众诉求的程度。但我也表明僵局会更多地阻碍不受欢迎而非受欢迎政策的形成。因此,在僵局十分紧张的时期,政策结果会与大众偏好更加一致,因为这些有着最广泛的大众支持的政策能够形成足够的政治压力来克服“僵局过滤器”(gridlock filter)。
政治环境(political conditions),诸如政党体制变动、国会中的多数党力量以及僵局等,有助于解释一些不同时期政策回应性的非预期模式。比如,我曾预测,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担任总统时期,对穷人和中产阶层有着高回应度,但却发现了对所有收入阶层的低回应度。我在第七章表明,在这个时期的强民主党控制隔绝了约翰逊政府的公众压力,使得民主党能够追求它自己的政策议程——一个既能够纳入更广泛的大众政策,如医疗和联邦教育援助,也能纳入更广泛的不受欢迎的政策,如对贫困和移民改革(的许多方面)的议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W.布什最初管理的那些年,这段时期以一个席位平均分配的国会和2000年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高度极化的政治气候为特点。这个时期的政策结果对所有收入阶层的偏好都有很高的回应性——这与乔治·W.布什的前任总统们任职期间缺乏对穷人和中产阶层的回应截然不同。但是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示:这个独特的情况是短暂的,而且对大众偏好的回应性在乔治·W.布什任职的中期、强共和党控制时期迅速下跌。因此,政治环境而不是乔治·W.布什政府回应弱势群体偏好的倾向,解释了这个不符合预期的发现。
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分析所得的回应性模式,支撑了以下观点,即政党是被对制定他们所偏好的政策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激进主义者和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策最大化者”(policy maximizers)。我的发现似乎支持了这个观点,即美国的政党已经从关注大众偏好的具有广泛基础的、选票最大化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密集的、狭窄的“政策要求者”(policy demanders)联合。然而政党和政治家必须被政治环境驱动来回应大众偏好的事实,意味着他们能够被那些环境所迫。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提高政治竞争性的改革,能够强化选举邻近性和国会均等政党划分的益处,并从而同等增强政策制定者对贫穷和富裕群体的回应性。
在我的结论章节,我进一步探讨了美国政治中金钱的角色,并寻求识别最有希望提升代表性平等的战略。我的重点在于公民在政治体系的参与上,富裕的美国人更可能投票,志愿参与政治运动,并且为政治事由捐献。但捐钱是唯一能够反映前章所提到的代表性不平等的政治参与组成部分。与其他对政治影响的研究相似的是,这个发现意味着对富裕群体不成比例的偏好回应性不能归因于他们更高的出席率或对政治运动更大的参与。金钱——政治的母乳——是代表性不平等的根源,而且随着政治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变得愈加昂贵,对为其提供必需资源的群体的回应性也随之增长。
在结尾,我尝试探索并梳理政治中的金钱流动,并就提升民主政府回应性和减弱代表性不平等的可能方法提出了建议。在这点上,即便是得出微薄的成果也很困难。选举财务改革(campaign finance reform)可以被比作挤气球,你在一个点推会让另一边鼓出来。而且,在人数减少的富裕群体中,收入和财富的愈益集中,扩大了早已笼罩的政治集权的阴影,正如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优势地位。
但是,美国民主并没有在1776年革命后迎来春天。选举权在一开始仅限于白人、男性有产者,这个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多世纪——穷人、妇女和非裔美国人才被纳入选民中。而根据我的分析,决策权并没有沿着这个有希望的路径走下去。在最近的几十年,政策制定者对富裕群体偏好的回应性在稳定增长,但对不那么富裕群体的回应性则没有这样的变化。这些年,美国在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种族多样性、教育系统的不足,以及新全球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崛起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强烈取决于谁的偏好指导着政策制定,而这些政策反过来会显著左右具优势或者不具优势的美国人的生活环境。
几十年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写道:“在这个国家,我们要么实现民主,要么让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被称为“新镀金时代”。美国的财富事实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比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严重。在这本书中,我考察了美国个体的财富资源与他们的政治权力的关系,试图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现代美国印证了布兰代斯大法官的断言。
每个社会的公民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但是民主社会一般被认为能够容纳相当程度的政治平等,即便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在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公式中,民主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是“视政府对其公民偏好的持续回应为政治平等的表现”。这个政治平等的理念在经济不平等面前或许不可能完全实现——在每个民主国家,拥有更多资源的公民更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但是一个社会中政治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加剧或减轻它的条件,能够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许多的民主质量信息。
我在本书的目标是通过考察由美国公众所表达的政策偏好与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者所采用的政策之间的关系,来展示和解释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代表性的不同模式。为此,我收集了一个反映美国不同收入阶层政策偏好的调查数据库。这些数据反映了成百上千的受访者对政府各种政策的回答——从提高最低工资到限制堕胎,再到美国向波斯尼亚派军。在随后的章节,我通过比较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对特定国家政策变动的诉求与由总统和国会决定的实际政策进程来分析这些数据。而我的发现很难与达尔民主公式中的政治平等概念相符合。美国政府确实对公众的偏好进行了回应,但这种回应强烈倾向于最富裕的公民群体。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似乎并未对政府采取或未采取的政策有什么本质的影响。
正如我要在后面所讲的那样,代表性不平等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环境及不同政策领域下广泛存在。然而也有例外,也有更倒向于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代表性。在识别这些情形时,我不仅想表明美国代表性不平等的变化,还想找出提高政府政策制定者在全体美国人民中的回应的平等性的更好方法。
本书计划
我首先要强调民主国家中大众意见所扮演的角色。许多观察者把调查受访者表达的政策偏好很大程度上视为消息不灵通的“无态度”(nonattitudes)。在公众对大众事务了解度和参与度低的情况下,我询问了大众政策偏好是否值得左右政府政策。第一章通过对公共舆论学者提出的“大众无知论”(public ignorance)的讨论来开始这个问题。我认为尽管大众很难达到许多观察者对公民知识和参与度的标准,但美国人在大众观点调查中所表达的政策偏好——作为美国评判民主回应性程度的一个标准,在事实上应该得到尊重。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该总是遵从多数意见,但它确实意味着大众政策与公众偏好的实质性偏差是民主治理失败的初步指标,并且政策制定者对优势群体偏好回应的不平等也是违背民主平等规则的一个基本指标。
第二章描述了我研究民主代表性的方法。我首先考虑了识别一系列现实和潜在的既不太泛(如哪些美国人拥有有意义的观点这样次要且模糊的议题)也不太窄(如政治行动者没有被纳入政府议程中)的议题的困难。随后我描述了调查数据和政策结果编码,这些是我的研究的基础。最后,第二章还强调了评估政府对公众回应性的替代性方法的优劣势。我还特别指出了使用现实政策而非国会投票作为利益结果(outcome of interests)的好处。首先,考察国会唱名表决(代表性分析中的常用方法)不能将政府议程设置权的重要性纳入其中,议程设置权决定了在众多潜在议题中选择或忽略哪个。其次,许多国会唱名表决议题的关键政策决定是在立法过程之前闭门决定的。最后,我还指出要理解代表性不平等,需要对离散的政策决定而不是宽泛的对自由或保守倾向的分析。富裕的美国人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保守,而在诸如堕胎、同性恋权利以及外国援助等问题上更自由化。相应的,当这些相反的议题都纳入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指标时,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偏好差异就会被抵消。
在第三章,我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评估了公众偏好和政府政策的关联。我发现了政策结果和富裕群体之间存在着相当强的关联,与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则有更弱的关联。我还发现政策结果与后者偏好的关联大部分还是基于后者与前者有共同的偏好。当不那么富裕的美国群体持有与富裕群体不同的偏好时,政策对富裕群体的回应仍然很强,但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几乎为零。
我对政策回应性的考察还表明,偏好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在高度支持或者反对政策变动上是最明显的。比如,如果意见是较为平均地分配的话,20%以内的差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比如40%与60%的支持率之间的差别),而更大的差异,比如意见一边倒(如20%—40%或60%—80%的支持率)时则会有更大的影响。这种规律意味着公众偏好的政治意义更多的在于相关群体支持或反对的“程度”上,而不是简单的多数支持或反对的“差异”上。
第三章也强调了我发现的代表性不平等的替代解释。首先,我展示了我的政策偏好的测量信度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异不大,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导致的差异也如此(比如我的数据库中对某一问题有观点的不同收入群体受访者比例)。其次,观点强度的差异(比如在多大程度上受访者的偏好是“非常”或者“有点”)也不能解释代表性不平等的差异规律。最后,我强调了偏好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联不仅反映了大众(或者说是大众的富裕部分)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还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精英对大众偏好的影响的可能性。根据从我的数据库中得出的诸多证明和对前人的研究,我指出尽管这些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观察偏好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联,大众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更能解释我在分析中所观察到的关联。
第三章表明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间存在着大量的代表性不平等,而第四章则观察了这种不平等在实质性议题领域内的分布。我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我所检验的四个议题领域内的不平等回应性的整体模式是相似的。对每个政策领域偏好与政策结果的仔细观察,表明了如果政府能够平等地反映全体美国人的偏好的话,政府政策会如何变化。比如,在经济领域,我们会期望有一个更累进的税收体系、更严格的公司管制和更高的最低工资;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更具保护性的贸易体制和更少的国外援助;在涉及宗教或道德问题的政策上,比如堕胎和同性恋权利,则会更加保守。在这些政策上,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是大多数支持哪边的问题。然而像第三章所表明的那样,支持程度(或反对程度)只是政治性的间接影响,取决于是否大多数支持或反对这个政策。
我在第四章的分析展示了一个社会福利案例,是一个对代表性不平等一般模式的局部的例外。在社会安全问题、医疗、教育券以及市政工程支出上,政策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偏好回应度要高于我考察的其他议题领域。我指出原因在于穷人和中产阶层美国人在这些议题上有利益集团同盟,在其他领域则没有这样的同盟。美国退休工人协会(AARP)、教师联盟、卫生行业以及其他游说团体在这些问题上与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群体偏好一致,并且致力于将政策结果向非优势群体和利益集团更希望的方向推动。
第四章中利益集团的识别对于解释代表性不平等同等重要,这引起了第五章对利益集团角色的更广泛的考察。针对数据库中的每个政策变动,我开发了一个利益集团结盟指数(measure of interest-group alignment)来做这些分析。利用这个指数,我发现当利益集团联盟与政策结果强烈相关时,它们并不能解释先前章节里所展示的代表性不平等。而当利益集团更多地参与到某一议题时,大众偏好(或者说大众中的富裕群体)或多或少有影响,但也并不能解释(代表性不平等)。相反,我认为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影响政府政策的基本平行的渠道。当利益集团和富裕群体达成一致时,政策制定者很可能服从这个诉求。而当这两者的目的不一致时,他们会一贯地阻止政策变化——不管是利益集团还是支持维持现状的富裕群体。我总结如下:利益集团有助于解释我的数据库中政策结果模式,并能解释那些反常的案例,如那些与穷人或中产阶层而非富裕群体的偏好更一致的情况。但是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对政策回应性中的贫富偏差做出解释。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我考察了政治条件(political conditions)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政策回应性的影响。第六章从对数据库增加和结构修改部分的描述开始,来更好地评估代表性是如何随着时间和政治背景的变化而不同。随后我考察了选举周期的角色,表明对所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在总统选举年都是最高的,且最不富裕群体的“代表性激增”最大。相应的,代表性不平等在总统选举年是最低的(即便是在这些时期,富裕人群的偏好与政策仍保持着最强的关联,而低收入人群的偏好与政策关联最弱)。我也在第六章表明,对富裕群体的偏好回应性在总统控制权在政党之间转移后的第一年会增加。这个模式对中产阶层的效力要弱得多,而对穷人则完全行不通。因此,这种政策制定的波动——典型地刻画了华盛顿的新政党政权特征——倾向于迎合富裕群体而非其他人的偏好。
最后,通过对共和党控制国会和总统时期与民主党主导联邦政府时期的比较,第六章探讨了政党对代表性的影响。民主党长期被视为工薪阶层政党,相较于富裕群体,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也一贯被更多地视为民主党支持者。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民主党执政时,代表性不平等更大,对所有收入阶层(包括穷人)的回应性更低。对那些解释政党代表性模式的特定问题的分析表明,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两党核心政策承诺的后果,这些承诺包括不受大众欢迎的增税(和受欢迎的减税)、批准里根国防建设法案、支持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至少在它们早期的时候),反对放松移民管制,以及支持乔治·W.布什的“基于信仰的行动”。除此之外,民主党与有组织的劳工的长期联盟也随着该党在过去几十年中采取了对管制和贸易政策更市场化的政策走向而受到侵蚀(例如民主党执政下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在社会福利领域,一个不同的政党模式也产生了,但却是一个民主党执政对穷人回应性更高和共和党执政对富人回应性更高的情况(对中产阶层的政策回应性在两党之间差不多)。
值得强调的是,共和党执政比民主党执政对穷人更强的政策回应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物质上更有利于穷人的政策更有可能在共和党掌握权力时被采用。我在第六章表明,有着明显的倾向底层再分配作用的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更有可能被采用,而那些具有倾向高层的再分配作用的政策,比如减少房产税,在共和党执政时更常见。但这些再分配政策,尽管很重要,仅仅是我的数据库中政策的一小部分,而且对这些政策的偏好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持久和强烈。
第七章强调了过去几十年间更加广泛的政策回应性趋势。我曾预期代表性不平等在美国是随着经济不平等而增长的。我也确实在我涵盖了过去40年的数据库中,发现了这种对富裕群体而不是其他收入群体回应性稳定增加的证据。但是故事远比这复杂,而且短期的政治条件波动对掩盖长期趋势以及形成对所有收入群体回应性有着重要影响。第七章特别展示了一个席位平均分配的国会,它一视同仁地提升对穷人、中产阶层、富裕群体的回应性,而政党和政治家却(暂时地)忽略了他们在获取大众支持时所做的承诺。我还表明政党极化导致的政策僵局还会出人意料地提升回应性。这种僵局会减少政策变动,并且相应地降低了联邦政府重视公众诉求的程度。但我也表明僵局会更多地阻碍不受欢迎而非受欢迎政策的形成。因此,在僵局十分紧张的时期,政策结果会与大众偏好更加一致,因为这些有着最广泛的大众支持的政策能够形成足够的政治压力来克服“僵局过滤器”(gridlock filter)。
政治环境(political conditions),诸如政党体制变动、国会中的多数党力量以及僵局等,有助于解释一些不同时期政策回应性的非预期模式。比如,我曾预测,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担任总统时期,对穷人和中产阶层有着高回应度,但却发现了对所有收入阶层的低回应度。我在第七章表明,在这个时期的强民主党控制隔绝了约翰逊政府的公众压力,使得民主党能够追求它自己的政策议程——一个既能够纳入更广泛的大众政策,如医疗和联邦教育援助,也能纳入更广泛的不受欢迎的政策,如对贫困和移民改革(的许多方面)的议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W.布什最初管理的那些年,这段时期以一个席位平均分配的国会和2000年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高度极化的政治气候为特点。这个时期的政策结果对所有收入阶层的偏好都有很高的回应性——这与乔治·W.布什的前任总统们任职期间缺乏对穷人和中产阶层的回应截然不同。但是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示:这个独特的情况是短暂的,而且对大众偏好的回应性在乔治·W.布什任职的中期、强共和党控制时期迅速下跌。因此,政治环境而不是乔治·W.布什政府回应弱势群体偏好的倾向,解释了这个不符合预期的发现。
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分析所得的回应性模式,支撑了以下观点,即政党是被对制定他们所偏好的政策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激进主义者和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策最大化者”(policy maximizers)。我的发现似乎支持了这个观点,即美国的政党已经从关注大众偏好的具有广泛基础的、选票最大化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密集的、狭窄的“政策要求者”(policy demanders)联合。然而政党和政治家必须被政治环境驱动来回应大众偏好的事实,意味着他们能够被那些环境所迫。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提高政治竞争性的改革,能够强化选举邻近性和国会均等政党划分的益处,并从而同等增强政策制定者对贫穷和富裕群体的回应性。
在我的结论章节,我进一步探讨了美国政治中金钱的角色,并寻求识别最有希望提升代表性平等的战略。我的重点在于公民在政治体系的参与上,富裕的美国人更可能投票,志愿参与政治运动,并且为政治事由捐献。但捐钱是唯一能够反映前章所提到的代表性不平等的政治参与组成部分。与其他对政治影响的研究相似的是,这个发现意味着对富裕群体不成比例的偏好回应性不能归因于他们更高的出席率或对政治运动更大的参与。金钱——政治的母乳——是代表性不平等的根源,而且随着政治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变得愈加昂贵,对为其提供必需资源的群体的回应性也随之增长。
在结尾,我尝试探索并梳理政治中的金钱流动,并就提升民主政府回应性和减弱代表性不平等的可能方法提出了建议。在这点上,即便是得出微薄的成果也很困难。选举财务改革(campaign finance reform)可以被比作挤气球,你在一个点推会让另一边鼓出来。而且,在人数减少的富裕群体中,收入和财富的愈益集中,扩大了早已笼罩的政治集权的阴影,正如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优势地位。
但是,美国民主并没有在1776年革命后迎来春天。选举权在一开始仅限于白人、男性有产者,这个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多世纪——穷人、妇女和非裔美国人才被纳入选民中。而根据我的分析,决策权并没有沿着这个有希望的路径走下去。在最近的几十年,政策制定者对富裕群体偏好的回应性在稳定增长,但对不那么富裕群体的回应性则没有这样的变化。这些年,美国在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种族多样性、教育系统的不足,以及新全球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崛起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强烈取决于谁的偏好指导着政策制定,而这些政策反过来会显著左右具优势或者不具优势的美国人的生活环境。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公民能力和民主决策制定
本书探讨美国公众希望政府所做的事与政府实际做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我分析大众偏好和政府政策的关系,以确定政府回应被统治者意愿的条件,以及识别政府回应的被统治者的群体。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展示了政策制定者对更富裕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偏好回应上大量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有着现实影响,还对我们理解生活其中的社会有着规范性意义。
激进民主的核心思想是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应该被公民广泛和几乎平等地享有,即公民普遍能够(或几乎平等地)行使这个权力。因此,基于我们对大众意见的本质和美国公民中等水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认知,在开始评估大众偏好和他们与政府决策制定的关系、识别由于对民主的不同理解有这些偏好的角色,以及评估大众在民主治理过程中能够被合理期待的角色之前,这个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自柏拉图始,对民主的批评质疑了公民指导他们的政治统治者的能力。如果公民对政治议题的偏好是变化无常或者是错误表达的,或者他们太容易被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平等的影响力在政府决策制定中导致的结果,即使不是个灾难,也不是人们乐见其成的。然而,虽然对代表性平等的呼吁可能来自规范视角,但大众的局限可能对有意义的民主的实现产生现实的妨碍。如果大众不能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形成明智的偏好,那么我在随后章节中所展示的代表性不平等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不同的规范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大众回应的不平等反映出的是大众首先在形成明智的政策偏好上的失败,而并不是政府决策制定者在回应大众上的缺陷。
在本章中我强调了公民能力的问题。在大量对大众意见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我指出民主的批评者在他们对公民有限的政治知识和能力的认识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这些认识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上是错误的。我指出,公民只需要在他们最关心的子议题有合理程度的见识即可,并不需要充分了解和关注议程上的每个问题。此外,公民不需要变成公共政策在技术复杂性方面的专家,而只需要能够识别那些代表他们一般的价值观和观点,并能指导他们形成他们的政治偏好的专家即可。最后,当个体的偏好被加总时,个体公民的政治知识缺陷状况会缓解;集体观点会比集合它的个体观点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测和更令人信服。简而言之,大众偏好尽管是不完美的,但仍然构成民主决策制定的合理基础。
正如我指明的,如果大众在形成政策偏好上是有能力胜任的,那么政府政策在回应这些偏好上的失败,或者政策制定者在回应更富裕或者更不富裕美国人偏好上的明显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民主治理的失败。尽管我们不期待或者不希望在每个问题上大众观点与政府政策完美一致,在回应大众偏好上的大量的和持续的不平等仍驳斥着我们对美国民主社会形象的认知。
接下来,我首先观察对民主的不同理解下大众所被分配的角色,然后基于已知的关于大众意见的本质和美国公民中等水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情况,评估了大众预期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个角色。在总结大众实际上能够完成在民主治理中它所被指派的功能后,我强调了在测量大众态度和评估政府对公民偏好回应性上的一些实际挑战。
公民能力和民主决策制定
本书探讨美国公众希望政府所做的事与政府实际做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我分析大众偏好和政府政策的关系,以确定政府回应被统治者意愿的条件,以及识别政府回应的被统治者的群体。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展示了政策制定者对更富裕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偏好回应上大量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有着现实影响,还对我们理解生活其中的社会有着规范性意义。
激进民主的核心思想是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应该被公民广泛和几乎平等地享有,即公民普遍能够(或几乎平等地)行使这个权力。因此,基于我们对大众意见的本质和美国公民中等水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认知,在开始评估大众偏好和他们与政府决策制定的关系、识别由于对民主的不同理解有这些偏好的角色,以及评估大众在民主治理过程中能够被合理期待的角色之前,这个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自柏拉图始,对民主的批评质疑了公民指导他们的政治统治者的能力。如果公民对政治议题的偏好是变化无常或者是错误表达的,或者他们太容易被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平等的影响力在政府决策制定中导致的结果,即使不是个灾难,也不是人们乐见其成的。然而,虽然对代表性平等的呼吁可能来自规范视角,但大众的局限可能对有意义的民主的实现产生现实的妨碍。如果大众不能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形成明智的偏好,那么我在随后章节中所展示的代表性不平等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不同的规范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大众回应的不平等反映出的是大众首先在形成明智的政策偏好上的失败,而并不是政府决策制定者在回应大众上的缺陷。
在本章中我强调了公民能力的问题。在大量对大众意见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我指出民主的批评者在他们对公民有限的政治知识和能力的认识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这些认识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上是错误的。我指出,公民只需要在他们最关心的子议题有合理程度的见识即可,并不需要充分了解和关注议程上的每个问题。此外,公民不需要变成公共政策在技术复杂性方面的专家,而只需要能够识别那些代表他们一般的价值观和观点,并能指导他们形成他们的政治偏好的专家即可。最后,当个体的偏好被加总时,个体公民的政治知识缺陷状况会缓解;集体观点会比集合它的个体观点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测和更令人信服。简而言之,大众偏好尽管是不完美的,但仍然构成民主决策制定的合理基础。
正如我指明的,如果大众在形成政策偏好上是有能力胜任的,那么政府政策在回应这些偏好上的失败,或者政策制定者在回应更富裕或者更不富裕美国人偏好上的明显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民主治理的失败。尽管我们不期待或者不希望在每个问题上大众观点与政府政策完美一致,在回应大众偏好上的大量的和持续的不平等仍驳斥着我们对美国民主社会形象的认知。
接下来,我首先观察对民主的不同理解下大众所被分配的角色,然后基于已知的关于大众意见的本质和美国公民中等水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情况,评估了大众预期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个角色。在总结大众实际上能够完成在民主治理中它所被指派的功能后,我强调了在测量大众态度和评估政府对公民偏好回应性上的一些实际挑战。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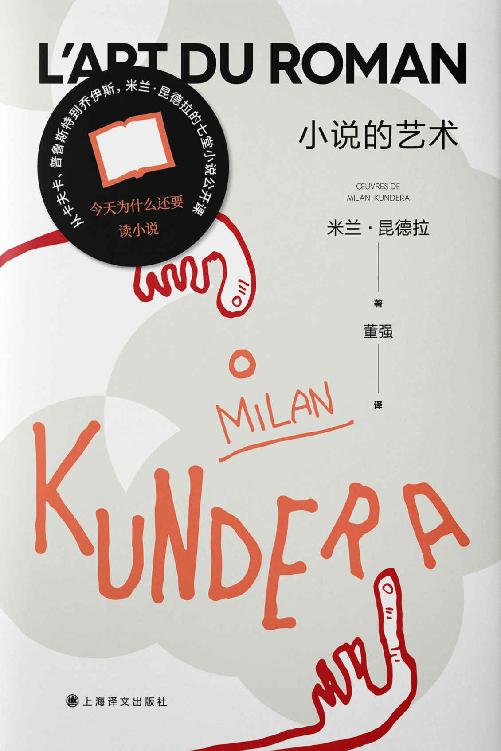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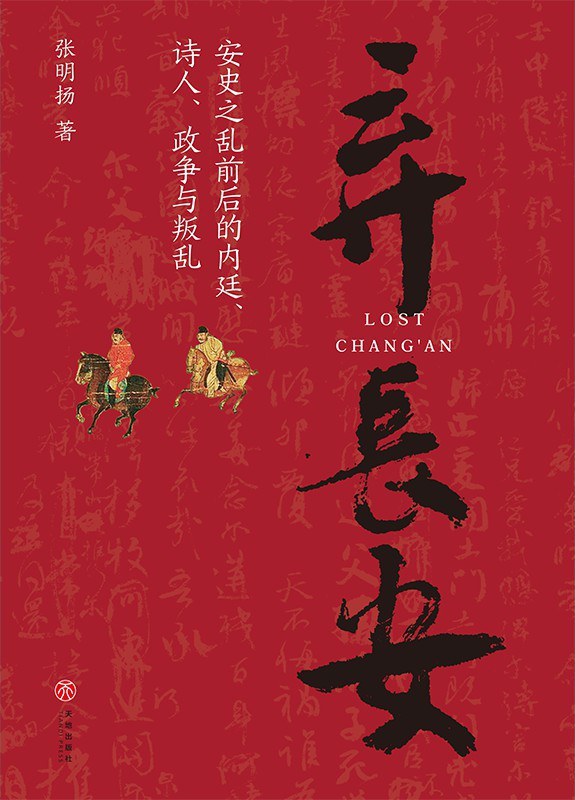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