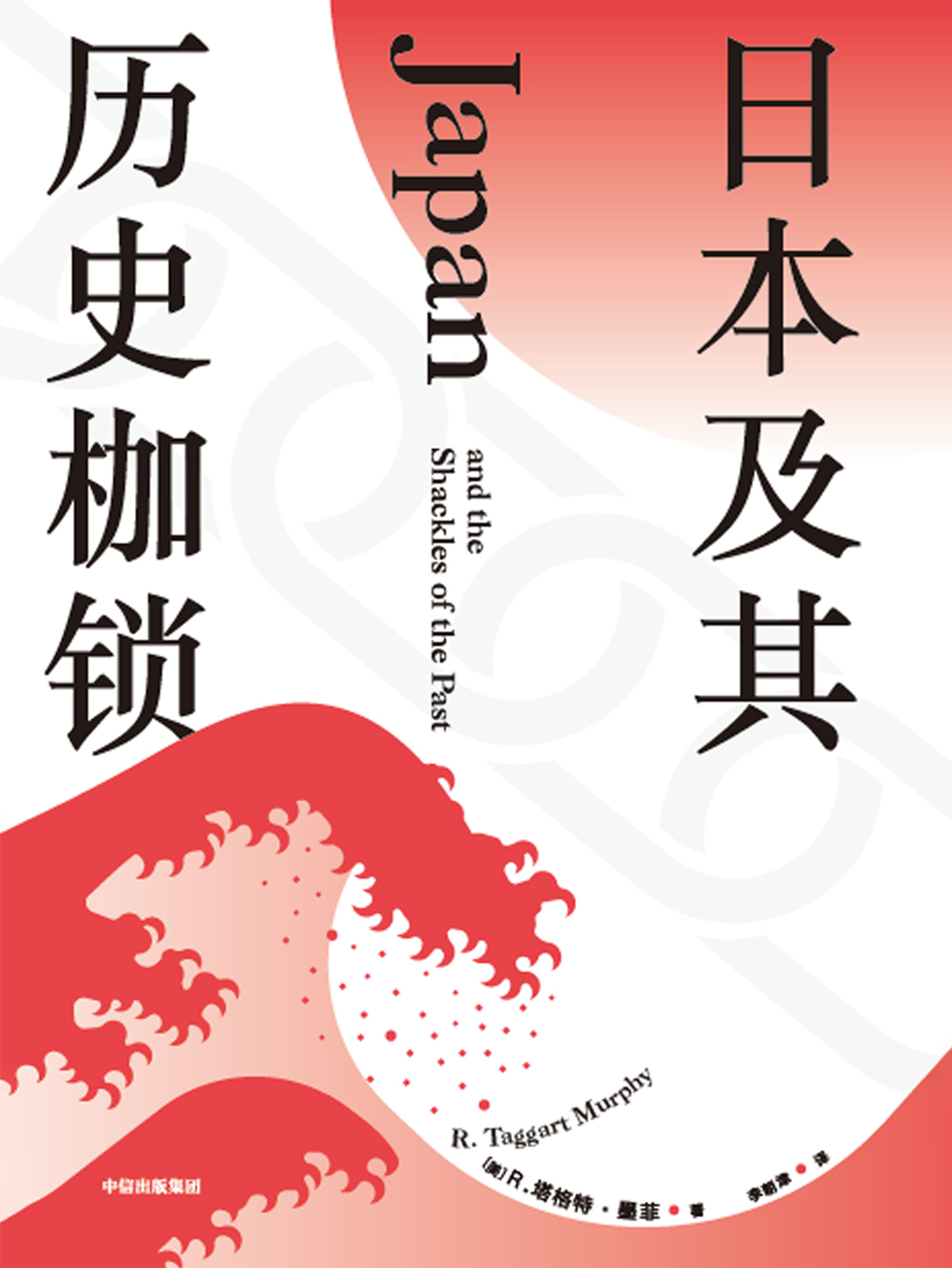
站在过去与未来十字路口上的日本 一手是从过去四百年政治史中继承的沉重锁链 一手握住传统审美与潮流文化带来的世界认同
—————————–
日本从1853年改革以来迅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给世界历史留下了许多鲜明的故事。今天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外部世界提起它时,人们感兴趣的是其传统艺术、饮食、时尚设计与动画产业;关于日本的政治与经济机构,更多的则是政府的无能、经济的低迷以及“日本第—”神话的倒塌。 为了寻找日本陷入困境的原因,塔格特·墨菲将目光投向从平安时代开始的政治经济史。日本的枷锁,早在1603年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时铸成,幕府统治对秩序与稳定的痴迷,将等级观念直接注入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不仅将全世界拖入战争的泥淖,也使现代日本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债务。 战后致力于高速经济发展的日本,也未曾摆脱这道历史枷锁的束缚。 尽管日本曾凭借其劳动体制、技术和资产赢得了海外市场,但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新型产品与服务模式,固守传统的日本企业开始停滞不前。有关国家神话的构建和战争叙事的谎言,以及安倍政府鼓动的排外情绪,亦为日本套上了新的枷锁。 打破日本枷锁的关键在哪里? 日本是否能够期望一位新领导者,以修复脆弱的日本经济,重建正当的对华、对美关系,并充分利用其文化优势和社会资源?作者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知日派”有关日本政治建构的历史,加上自身对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各边缘阶层的体察,试图寻找一个在枷锁中缓慢前行,却又富有生机活力的日本。
编辑推荐
1. 21世纪“知日派”了解近现代日本政治与文化的新作 牛津大学出版社“人人须知”系列丛书日本近代史篇,从德川幕府以来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两条并行线中了解日本。即使在今天,我们对日本的唯—兴趣经常停留在传统艺术、饮食、时尚设计与漫画中;提到日本的政府与商业机构,往往留下的是官员迟缓与无能的印象,或者是无法解决的经济与生态灾难。但日本历史对我们的启示仅仅是负面的吗?作者梳理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知日派”有关日本政治建构的历史,加上自身对于日本文化(从浮世绘、歌舞伎到漫画动画、电子游戏、偶像产业、色情服务业)的犀利观察,试图寻找一个在枷锁中缓慢前行,却又富有生机活力的日本。 2. 回顾近代400年日本人蓄意为自己“创造困境”的历程 日本被历史束缚而寸步难行,这种观点已不新鲜。但在塔格特·墨菲看来,日本的“枷锁”无疑是整个国家有意识创造的,并且让其中一部分人从中困境中获益。从德川幕府创造严苛的等级社会以来,这种枷锁就已经被束缚了。在现代日本,统治的官员们习惯性地容忍矛盾,回避问题与冲突,用虚构的战争叙事来维持构建好的国家神话。 3. 有关现代日本出路的奇妙解答:只有羽生结弦才能救日本? 当“安倍经济学”未能挽救日本低迷的经济,政府精英倡导的怀旧情绪将国民拉向排外主义的泥潭,谁能够拯救枷锁中的日本?也许日本人可以期望一个“戴高乐式”的新领导者,在国内外政策上力挽狂澜。比如想象恢复正当、平等的日美关系,修复对华关系,并重视中产阶级与家庭妇女的社会力量。然而作者将目光投向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色:19岁的冬奥会花滑金牌得主羽生结弦。他从2011年的震灾中重拾生活,走向运动生涯的巅峰,并且凭借谦卑、友好的态度赢得世界各地的喜爱——这似乎是对于安倍政府以来日本政策有力的驳斥。 4.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像日本,我们该怎么办? 当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多数经济与人口问题,如老龄化、金融体系崩溃、货币政策失灵、生产产能过剩而利润降低……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特殊的一员,日本已经面对这些棘手难题20年之久,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反面教材”。当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开始变得与日本一样迟缓,当各国的统治精英们对问题与矛盾熟视无睹,我们该怎么办?日本历史枷锁锻造的轨迹,似乎给了我们寻根溯源的线索。
目录
封面
版权页
献给修
前言与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 历史枷锁的锻造
第一章 江户时期以前的日本
第二章 现代日本国家的孕育
第三章 从“维新”到占领
第四章 奇迹
第五章 高速增长体制
第六章 结果:有意或无心
第二部分 当今日本的枷锁
第七章 经济与金融
第八章 商业
第九章 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第十章 政治
第十一章 日本与世界
参考书目
版权页
献给修
前言与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 历史枷锁的锻造
第一章 江户时期以前的日本
第二章 现代日本国家的孕育
第三章 从“维新”到占领
第四章 奇迹
第五章 高速增长体制
第六章 结果:有意或无心
第二部分 当今日本的枷锁
第七章 经济与金融
第八章 商业
第九章 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第十章 政治
第十一章 日本与世界
参考书目
前言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人人须知”系列,本书成为其中之一。入选这个系列的主题都很有价值,日本当然也不例外。大卫·麦克布赖德邀请我来写作这本书时,我有点受宠若惊,但也有点不安。我担心稍微了解日本的人便不会翻开这样一本描写日本的书,其他人可能也会忽视。因为回到2010年,外部世界对日本唯一感兴趣的似乎就是它的文化:饮食、传统艺术、当代时尚设计和村上春树的小说,还有那些奇异的视频与漫画。除了日本人以及那些像我一样生活与之神秘交织的“怪人”之外,如果还有人对日本的政治、商业与经济感兴趣,也是将其当作警诫人的教训。我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日本给我们提供了各种经验教训,其中很多并非负面的。我以前发表的文章所关注的那些议题(如日本的政治、商业、经济等),现在似乎已经没人关心了。再多一本书可能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无法重新点燃这个国家曾经有的广泛魅力。
但大卫的邀请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做其他任何写作方式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将我对日本政治和经济的思考与人们似乎一直感兴趣的历史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我越是思考日本的信用创造如何转化为经济活动或日本在当今全球金融框架建设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这些问题我在其他书中也讨论过),就越是确信不可能孤立地理解这些事情。想了解日本现实的任何一个面相,就必须把握其整体的面貌。换言之,日本银行的货币供应量、日本企业的人事习惯、东京街头标新立异的时装、日本政治无休止的抢座椅游戏、日本数百年的锁国政策,这些问题都存在某种关联。大卫正给我机会找出这些联系。即便最后没有多少人读这本书,那也无妨,因为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考的机会,使我可以整理从15岁开始就让我着迷的思索。那时,我在陈旧而拥挤的羽田机场走下飞机,坐上长途汽车,沿途看见灰色的、快节奏的、行人如鲫的城市风貌,那一切是我平生没有见过的。因此,我认为这本书值得写。
在正式开始写作之前,一些事件证明,我关于日本再无人关注的判断似乎是错误的。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地震和海啸,这让它顿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生命陷入危险,而他们的英雄事迹与人道关怀让世界为之震动。但当核电站在灾难中被毁,关于其废墟的新闻逐步流出后,疑问开始出现。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既能唤起社会的凝聚力和纯粹的人性尊严,又能培养出一个领导阶层,在明知日本地处地震频发带的情况下,仍不可宽恕地建造这种致命的能源站,然后又轻忽其危险性,其所犯过失已无异于犯罪?
我继续往下写的时候,其他问题也开始浮现。其实,这些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讨论。为什么一个明显失能的政党在遭选民抛弃后不到4年又重新掌权?日本政府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右倾”,但为什么能实行最“左倾”的货币财政混合政策?东亚地区不断升级的口头挑衅是否预示着误判并最终导向战争?外来者(特别是美国)是否会被卷入冲突?或许,我已经不只是为自己而写。
如果这本书在提出(更不用说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有任何成功的地方,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路帮助我的人。第一个需要感谢的是大卫·麦克布赖德,他是第一个看到这个出版计划可行的人,而且不辞劳苦地找到我并给予鼓励。他一直耐心地关注书稿的进度并给我足够的时间完成。他知道我的抱负已经超越“人人须知”系列的目标,但并没有强迫我删减以适应丛书的要求,反而在紧要关头帮我修改书稿。马克·塞尔登与加万·麦考密克允许我在《亚太期刊:日本焦点》上发表一些作品,正是这些作品使得大卫开始关注我。马克阅读了我的一部分手稿,并一如既往地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也请罗伯特·阿利伯、槙原久美子与利奥·菲利普阅读了个别章节,他们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超乎我的想象。
开始写作时,我知道自己需要一个理想的读者,他不必在日本长时间生活过,甚至不必费力思考过日本,但他必须有兴趣和好奇心,这样的人是我首先需要找到的。乔治·威利亚德就是我要找的人,他不仅是理想的读者和亲爱的朋友,而且本身就是优秀的编辑和作家。我给他的每一章他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慷慨回应,对于我写的每一个字他都充分留意,这是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每当我词不达意或思路不够清晰,甚至他认为未臻完美时,他总是能给我很好的建议,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我也很感谢罗德尼·阿姆斯特朗。他在NBR日本论坛上就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做的精彩发言给我很大启发。后来,他花了几个小时很耐心地跟我讨论相关议题,仔细阅读了我就相关问题所写的东西并予以点评。
对于熟悉卡瑞尔·范·沃尔夫伦的读者而言,他们会清楚地看到他对我的影响。没有他的文章及个人典范,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他给了我无限的鼓励,他对本书最后两章给出的建议尤为重要。
完成初稿之后,我曾请两位好友帮助审阅整部文稿,告诉我有什么问题以及如何修正。吉雄福原与迈克·韦雷托是我认识的最能在两种文化间游刃有余的朋友,他们可以同时从日本和美国两种视角观察。我们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意见一致,他们也并非认同我写的所有东西,但他们对文稿仔细阅读并做出评论,这些都十分宝贵。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些人,他们应该完全不认识我。罗伯特·卡罗写的林登·约翰逊的传记包罗甚广,可惜当时并未完稿,我在撰写日本政治一章时辗转取得。卡罗的作品使我聚焦田中角荣在日本政治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种作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逐步展现出来。
我也向我哥哥亚历山大求助,希望他对书中的地图提出意见。亚历山大一生都在支持我,也在学问上不断激励我。他向我推荐了他的研究生尼古拉斯·A.珀杜。珀杜十分称职,我感谢他们两位。
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新加坡写成的,我亲爱的朋友罗伯特夫妇将他们美丽的家园向我开放,非常感谢他们。
这本书从初步构思到出版,我去了纽约好几次。我在商学院的同学槙原纯和以前的同事冈美美住在东村,每次我到纽约办事,他们都愿意让我住在他们家,深表感谢。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数十年来我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及其世界事务的重要渠道。美美的父亲冈高史是著名记者,曾为小泽一郎撰写传记。为寻找资料,我曾两度拜访他,与其讨论小泽的生平及重要性。
这本书大部分是在筑波大学东京校区的国际商务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办公室内撰写的。每当我对日本感到悲观时,这个课程(更不用说我的同事和学生)都会纠正我的想法。该课程最初由大学设立,最后得到文部科学省的支持,其存在反映了日本仍有人决心摆脱桎梏国家的枷锁。点亮蜡烛,总比诅咒黑暗来得积极。对于我和学生来说,学院的同事是我们思想上的激励、陪伴与支持。如果日本的命运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我们便不用担心了。我们有些学生来自日本以外的地方,如果决定对日关系的人都能像这些学生那样,我们也不用担心日本与外国的关系了。
初稿快要完成时,我已故父亲在“二战”时寄回家的书信,因为他妹妹、我亲爱的姑姑埃塞尔·古尔斯比的去世而为家人所知。我父亲是太平洋战争的见证者。他是数百万被送上战场的士兵中的一个,与开战完全没有关系,却可能葬身在那里。那些书信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它们展示了对我意义重大的一个人极其特别的一面——那一面我在成长过程中偶尔瞥见过。父亲写那些信时也只不过刚刚成年而已。因此,他对战争的许多评论(主要给他母亲看)包含了“我们为什么要打仗”之类的传统表达以及关于日本人的一些不太友好的言论,而且由于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菲律宾,有时也夹杂着他对当地的一些尖锐而有趣的观察。但在只给姐姐玛乔丽看的一封信中,他承认写信时会隐瞒一些事情以免让母亲不安。他告诉姐姐自己非常想家,“很多时候会感受到难以置信的苦闷和压力”,部队受到攻击时,他会产生莫名的恐惧。他写道:“(自己)会反胃,全身不由自主地发抖。”“很多人常常有类似的反应,只是很少说出来。”很明显,他讨厌日本人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但他接着写道,有一天晚上日本军队发动突袭,第二天早上他的部队组织反攻。走出小营地,他看见满地都是“支离破碎的身体,一些刚刚被杀的士兵的尸体曝露在外面,尸体变黑,浮肿发臭,伤口惨不忍睹”,但在其中一个士兵的尸体上,“放着一个卡片盒,里面有一张美丽的年轻日本女孩的照片”。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描绘了自己因为看到死去士兵身上的人性之光而痛苦挣扎,我被深深触动。他表达的这种情感类似于威尔弗雷德·欧文在《不可思议的聚会》(“Strange Meeting”)一诗中所表达的,后者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战诗。我父亲也许远远比不上欧文级别的诗人(谁又能呢?),但作为儿子,我可以理解他,可以想象他试图用文字、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讲述那些严肃问题时的模样。他的叙述以及背后的挣扎所呈现的力量和欧文的诗一样,都深深地触动了我。父亲这样写道:“我们不是壮硕的年轻人,没有有力的前臂和魁梧的身材,但也要拼尽全力与敌人搏斗。我们不是徒手作战,都要倚靠武器。很多人已经不再年轻。这不是一场武士格斗。即便是最虚弱的人,拿起机枪也要比徒手的超人更具杀伤力。我们搏斗不是靠身体的兴奋或刺激,而是用人类有史以来设计的最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当人类的身体碰上炽热的铅弹或冰冷的钢片时,它变得像纸一样单薄。”
因此,我要感谢父亲,既有实际的原因(我最早来日本,主要是因为一直与父亲合作的日本学者邀请他去他们大学访问一年),也是因为那些书信给我带来了重要信息。今天,在东亚你会听到很多关于国家荣耀与辉煌的胡言乱语,充斥着受害者的故事和历史错谬,使用的语言都带有排外和种族主义的色彩。说那些话的人,大部分没有战争经验(大概以后也不会有)。无论只是摆摆架势,还是他们内心真的是那样想的,他们对别人的愤怒总是胜过对自我的检视。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出问题,总是别人的错。整个气氛已被破坏,领袖们互相指责,而网站上到处都是捶胸顿足的民族主义者。地铁车厢内到处都是低级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广告,指责对岸的人不守诺言,而对岸的人则发现自己在聚集的地方受到了嘲弄。美国也许会对此表示不满,但它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它推翻了一个建了一半的明显脆弱的体系(而它给该地区带来了暂时解决问题的希望),美国这么做,是因为该体系意味着它要将海军基地迁回本国。
我会讲述这件事发生的过程,它是说明日本背景下的任何事情都不可孤立看待的又一个例子,而且可能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除非人们感觉到日本对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它对美国的倚赖已经让政治病态变得难以诊断和治疗的长期焦虑,否则军事基地问题及其破坏日本与邻国两代以来宝贵和平的方式,就只会以平时被描绘的样子呈现出来,使人显得忘恩负义、不称职和没有理性。
如果我真的能把日本各种关键问题的背景成功呈现出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面我所感谢的人(当然,错谬之处,概由我个人负责),还有过去数十年,在这个国家与我一起工作、玩乐和互相关爱的日本朋友,其中最主要的是我的终身伴侣川田修。像这样的致谢词,大部分在结尾时会感谢某位幕后人员,没有其支持与建议,要完成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对于本书而言,那个人就是川田,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他。
在整本书中,我都依从日本处理姓名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例如,田中角荣、安倍晋三)。
2014年7月写于东京
但大卫的邀请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做其他任何写作方式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将我对日本政治和经济的思考与人们似乎一直感兴趣的历史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我越是思考日本的信用创造如何转化为经济活动或日本在当今全球金融框架建设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这些问题我在其他书中也讨论过),就越是确信不可能孤立地理解这些事情。想了解日本现实的任何一个面相,就必须把握其整体的面貌。换言之,日本银行的货币供应量、日本企业的人事习惯、东京街头标新立异的时装、日本政治无休止的抢座椅游戏、日本数百年的锁国政策,这些问题都存在某种关联。大卫正给我机会找出这些联系。即便最后没有多少人读这本书,那也无妨,因为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考的机会,使我可以整理从15岁开始就让我着迷的思索。那时,我在陈旧而拥挤的羽田机场走下飞机,坐上长途汽车,沿途看见灰色的、快节奏的、行人如鲫的城市风貌,那一切是我平生没有见过的。因此,我认为这本书值得写。
在正式开始写作之前,一些事件证明,我关于日本再无人关注的判断似乎是错误的。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地震和海啸,这让它顿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生命陷入危险,而他们的英雄事迹与人道关怀让世界为之震动。但当核电站在灾难中被毁,关于其废墟的新闻逐步流出后,疑问开始出现。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既能唤起社会的凝聚力和纯粹的人性尊严,又能培养出一个领导阶层,在明知日本地处地震频发带的情况下,仍不可宽恕地建造这种致命的能源站,然后又轻忽其危险性,其所犯过失已无异于犯罪?
我继续往下写的时候,其他问题也开始浮现。其实,这些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讨论。为什么一个明显失能的政党在遭选民抛弃后不到4年又重新掌权?日本政府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右倾”,但为什么能实行最“左倾”的货币财政混合政策?东亚地区不断升级的口头挑衅是否预示着误判并最终导向战争?外来者(特别是美国)是否会被卷入冲突?或许,我已经不只是为自己而写。
如果这本书在提出(更不用说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有任何成功的地方,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路帮助我的人。第一个需要感谢的是大卫·麦克布赖德,他是第一个看到这个出版计划可行的人,而且不辞劳苦地找到我并给予鼓励。他一直耐心地关注书稿的进度并给我足够的时间完成。他知道我的抱负已经超越“人人须知”系列的目标,但并没有强迫我删减以适应丛书的要求,反而在紧要关头帮我修改书稿。马克·塞尔登与加万·麦考密克允许我在《亚太期刊:日本焦点》上发表一些作品,正是这些作品使得大卫开始关注我。马克阅读了我的一部分手稿,并一如既往地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也请罗伯特·阿利伯、槙原久美子与利奥·菲利普阅读了个别章节,他们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超乎我的想象。
开始写作时,我知道自己需要一个理想的读者,他不必在日本长时间生活过,甚至不必费力思考过日本,但他必须有兴趣和好奇心,这样的人是我首先需要找到的。乔治·威利亚德就是我要找的人,他不仅是理想的读者和亲爱的朋友,而且本身就是优秀的编辑和作家。我给他的每一章他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慷慨回应,对于我写的每一个字他都充分留意,这是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每当我词不达意或思路不够清晰,甚至他认为未臻完美时,他总是能给我很好的建议,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我也很感谢罗德尼·阿姆斯特朗。他在NBR日本论坛上就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做的精彩发言给我很大启发。后来,他花了几个小时很耐心地跟我讨论相关议题,仔细阅读了我就相关问题所写的东西并予以点评。
对于熟悉卡瑞尔·范·沃尔夫伦的读者而言,他们会清楚地看到他对我的影响。没有他的文章及个人典范,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他给了我无限的鼓励,他对本书最后两章给出的建议尤为重要。
完成初稿之后,我曾请两位好友帮助审阅整部文稿,告诉我有什么问题以及如何修正。吉雄福原与迈克·韦雷托是我认识的最能在两种文化间游刃有余的朋友,他们可以同时从日本和美国两种视角观察。我们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意见一致,他们也并非认同我写的所有东西,但他们对文稿仔细阅读并做出评论,这些都十分宝贵。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些人,他们应该完全不认识我。罗伯特·卡罗写的林登·约翰逊的传记包罗甚广,可惜当时并未完稿,我在撰写日本政治一章时辗转取得。卡罗的作品使我聚焦田中角荣在日本政治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种作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逐步展现出来。
我也向我哥哥亚历山大求助,希望他对书中的地图提出意见。亚历山大一生都在支持我,也在学问上不断激励我。他向我推荐了他的研究生尼古拉斯·A.珀杜。珀杜十分称职,我感谢他们两位。
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新加坡写成的,我亲爱的朋友罗伯特夫妇将他们美丽的家园向我开放,非常感谢他们。
这本书从初步构思到出版,我去了纽约好几次。我在商学院的同学槙原纯和以前的同事冈美美住在东村,每次我到纽约办事,他们都愿意让我住在他们家,深表感谢。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数十年来我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及其世界事务的重要渠道。美美的父亲冈高史是著名记者,曾为小泽一郎撰写传记。为寻找资料,我曾两度拜访他,与其讨论小泽的生平及重要性。
这本书大部分是在筑波大学东京校区的国际商务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办公室内撰写的。每当我对日本感到悲观时,这个课程(更不用说我的同事和学生)都会纠正我的想法。该课程最初由大学设立,最后得到文部科学省的支持,其存在反映了日本仍有人决心摆脱桎梏国家的枷锁。点亮蜡烛,总比诅咒黑暗来得积极。对于我和学生来说,学院的同事是我们思想上的激励、陪伴与支持。如果日本的命运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我们便不用担心了。我们有些学生来自日本以外的地方,如果决定对日关系的人都能像这些学生那样,我们也不用担心日本与外国的关系了。
初稿快要完成时,我已故父亲在“二战”时寄回家的书信,因为他妹妹、我亲爱的姑姑埃塞尔·古尔斯比的去世而为家人所知。我父亲是太平洋战争的见证者。他是数百万被送上战场的士兵中的一个,与开战完全没有关系,却可能葬身在那里。那些书信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它们展示了对我意义重大的一个人极其特别的一面——那一面我在成长过程中偶尔瞥见过。父亲写那些信时也只不过刚刚成年而已。因此,他对战争的许多评论(主要给他母亲看)包含了“我们为什么要打仗”之类的传统表达以及关于日本人的一些不太友好的言论,而且由于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菲律宾,有时也夹杂着他对当地的一些尖锐而有趣的观察。但在只给姐姐玛乔丽看的一封信中,他承认写信时会隐瞒一些事情以免让母亲不安。他告诉姐姐自己非常想家,“很多时候会感受到难以置信的苦闷和压力”,部队受到攻击时,他会产生莫名的恐惧。他写道:“(自己)会反胃,全身不由自主地发抖。”“很多人常常有类似的反应,只是很少说出来。”很明显,他讨厌日本人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但他接着写道,有一天晚上日本军队发动突袭,第二天早上他的部队组织反攻。走出小营地,他看见满地都是“支离破碎的身体,一些刚刚被杀的士兵的尸体曝露在外面,尸体变黑,浮肿发臭,伤口惨不忍睹”,但在其中一个士兵的尸体上,“放着一个卡片盒,里面有一张美丽的年轻日本女孩的照片”。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描绘了自己因为看到死去士兵身上的人性之光而痛苦挣扎,我被深深触动。他表达的这种情感类似于威尔弗雷德·欧文在《不可思议的聚会》(“Strange Meeting”)一诗中所表达的,后者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战诗。我父亲也许远远比不上欧文级别的诗人(谁又能呢?),但作为儿子,我可以理解他,可以想象他试图用文字、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讲述那些严肃问题时的模样。他的叙述以及背后的挣扎所呈现的力量和欧文的诗一样,都深深地触动了我。父亲这样写道:“我们不是壮硕的年轻人,没有有力的前臂和魁梧的身材,但也要拼尽全力与敌人搏斗。我们不是徒手作战,都要倚靠武器。很多人已经不再年轻。这不是一场武士格斗。即便是最虚弱的人,拿起机枪也要比徒手的超人更具杀伤力。我们搏斗不是靠身体的兴奋或刺激,而是用人类有史以来设计的最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当人类的身体碰上炽热的铅弹或冰冷的钢片时,它变得像纸一样单薄。”
因此,我要感谢父亲,既有实际的原因(我最早来日本,主要是因为一直与父亲合作的日本学者邀请他去他们大学访问一年),也是因为那些书信给我带来了重要信息。今天,在东亚你会听到很多关于国家荣耀与辉煌的胡言乱语,充斥着受害者的故事和历史错谬,使用的语言都带有排外和种族主义的色彩。说那些话的人,大部分没有战争经验(大概以后也不会有)。无论只是摆摆架势,还是他们内心真的是那样想的,他们对别人的愤怒总是胜过对自我的检视。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出问题,总是别人的错。整个气氛已被破坏,领袖们互相指责,而网站上到处都是捶胸顿足的民族主义者。地铁车厢内到处都是低级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广告,指责对岸的人不守诺言,而对岸的人则发现自己在聚集的地方受到了嘲弄。美国也许会对此表示不满,但它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它推翻了一个建了一半的明显脆弱的体系(而它给该地区带来了暂时解决问题的希望),美国这么做,是因为该体系意味着它要将海军基地迁回本国。
我会讲述这件事发生的过程,它是说明日本背景下的任何事情都不可孤立看待的又一个例子,而且可能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除非人们感觉到日本对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它对美国的倚赖已经让政治病态变得难以诊断和治疗的长期焦虑,否则军事基地问题及其破坏日本与邻国两代以来宝贵和平的方式,就只会以平时被描绘的样子呈现出来,使人显得忘恩负义、不称职和没有理性。
如果我真的能把日本各种关键问题的背景成功呈现出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面我所感谢的人(当然,错谬之处,概由我个人负责),还有过去数十年,在这个国家与我一起工作、玩乐和互相关爱的日本朋友,其中最主要的是我的终身伴侣川田修。像这样的致谢词,大部分在结尾时会感谢某位幕后人员,没有其支持与建议,要完成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对于本书而言,那个人就是川田,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他。
在整本书中,我都依从日本处理姓名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例如,田中角荣、安倍晋三)。
2014年7月写于东京
精彩书摘
日本群岛在欧亚大陆外围绵延近2000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相对于大陆的位置不远不近,相当优越:不算太远,故可以吸收大陆上各项发展成果;不算太近,故可以避免在文化或军事上为其掣肘。有人会将二者的关系与罗马帝国时期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的关系,或稍后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相比。无论如何,当一个社会与一个文明中心比邻而居,要如何应付其强大的吸引力,日本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在最近几个世纪,日本对欧亚大陆的冲击不亚于后者对它的影响。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位于边缘位置,游离于已知的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外来侵略发生在13世纪,当时忽必烈远征日本,几乎将其征服。突如其来的“神风”摧毁了忽必烈的战舰,日本因此逃过一劫,躲过欧亚大陆各地所遭受的命运,不用屈膝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
在日本古代历史上,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在科技和政治上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在其文化圈外围成长。日本从欧亚大陆吸收借鉴的东西(规模相当可观),大多经由朝鲜这个比它更小的国家传入。这种模式塑造了日本吸收和内化大陆体制的方法。当然,我们几乎不可能条分缕析地探清这些体制的来源:哪些来自朝鲜,哪些来自中国,哪些又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例如,大乘佛教经由中国和朝鲜来到日本,而大乘佛教的源头又可追溯到古希腊影响下的巴克特里亚,后者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相关研究的另一个阻力是过去150年来留下的包袱,日本与朝鲜之间相互怨怼、轻蔑,甚至不加掩饰地仇恨,不但妨碍了双方建立近代史史实的共识,亦使得两国之间早期关系的研究难以推进。只要尝试在日本文化及制度中寻找朝鲜元素,马上会引起极大的争议。在韩国,肯定韩国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日本殖民遗留下的影响,亦会导致强烈的争议。
在日本古代历史上,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在科技和政治上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在其文化圈外围成长。日本从欧亚大陆吸收借鉴的东西(规模相当可观),大多经由朝鲜这个比它更小的国家传入。这种模式塑造了日本吸收和内化大陆体制的方法。当然,我们几乎不可能条分缕析地探清这些体制的来源:哪些来自朝鲜,哪些来自中国,哪些又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例如,大乘佛教经由中国和朝鲜来到日本,而大乘佛教的源头又可追溯到古希腊影响下的巴克特里亚,后者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相关研究的另一个阻力是过去150年来留下的包袱,日本与朝鲜之间相互怨怼、轻蔑,甚至不加掩饰地仇恨,不但妨碍了双方建立近代史史实的共识,亦使得两国之间早期关系的研究难以推进。只要尝试在日本文化及制度中寻找朝鲜元素,马上会引起极大的争议。在韩国,肯定韩国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日本殖民遗留下的影响,亦会导致强烈的争议。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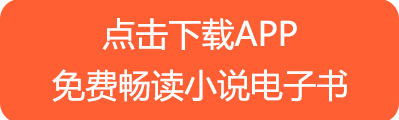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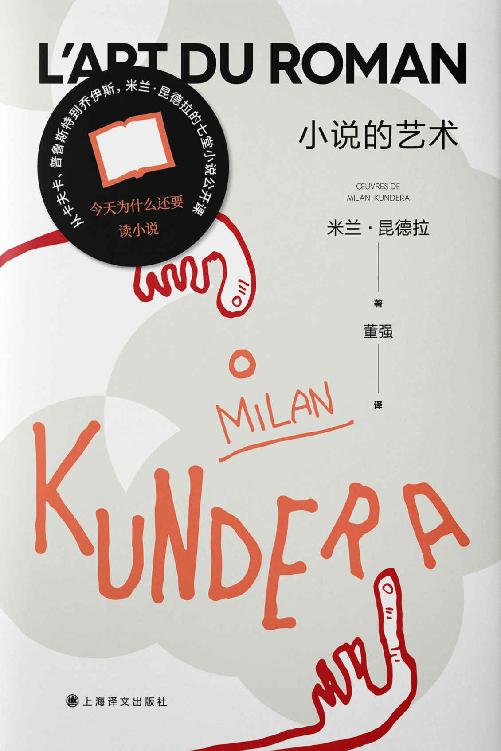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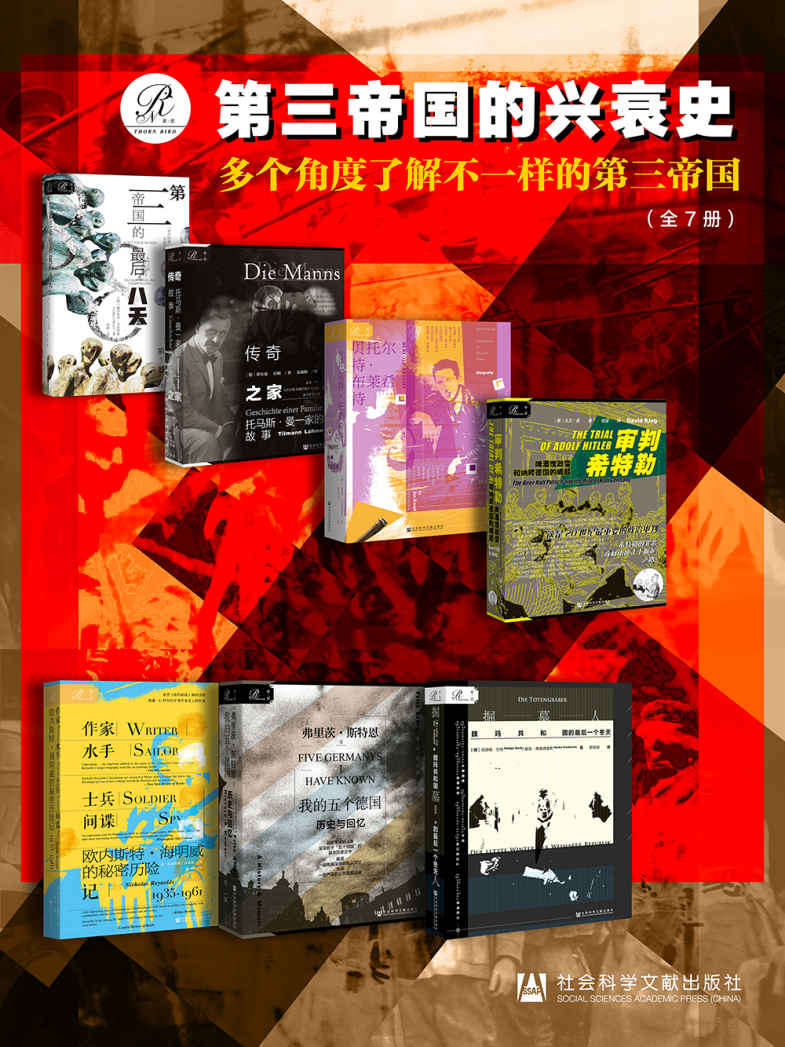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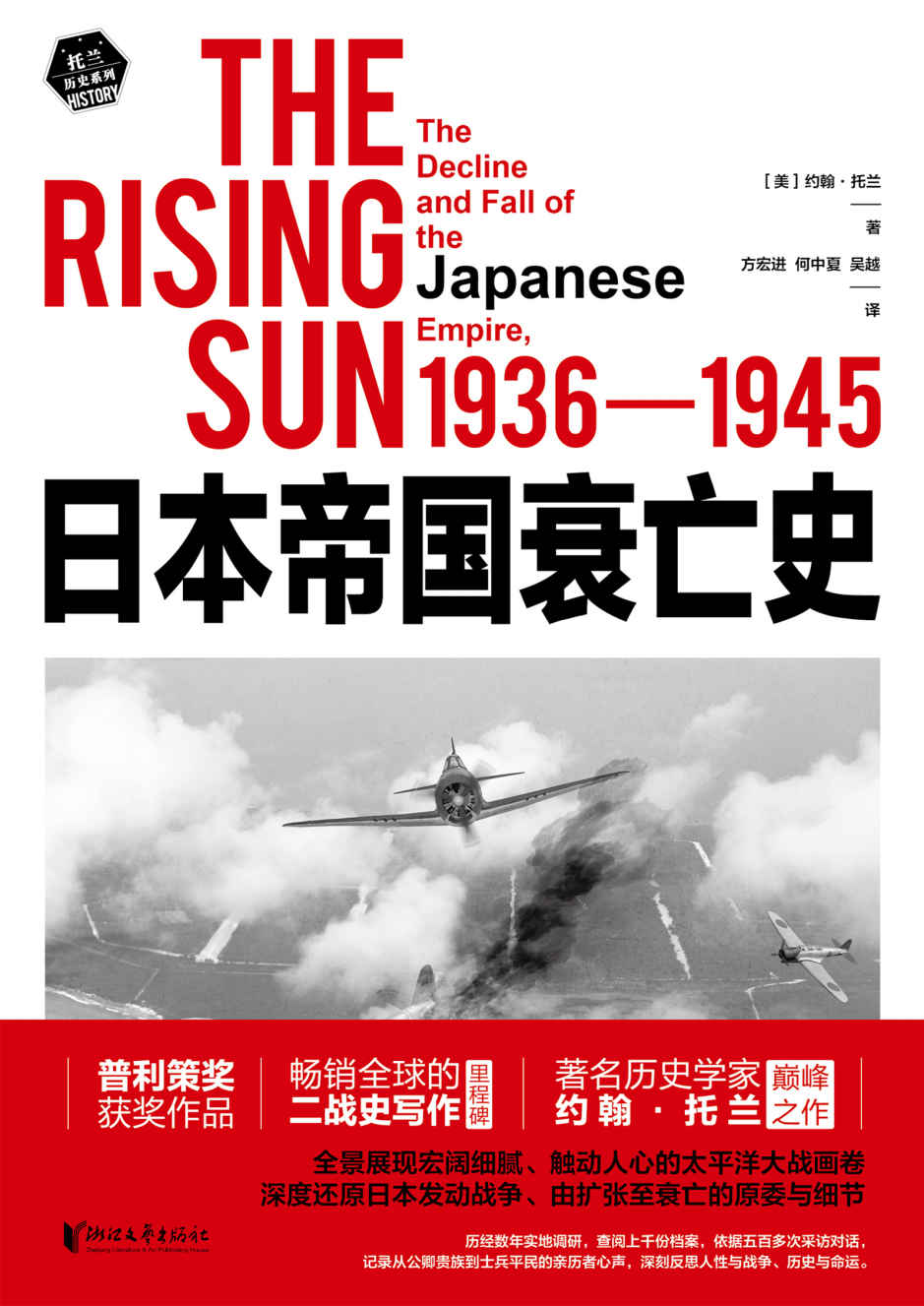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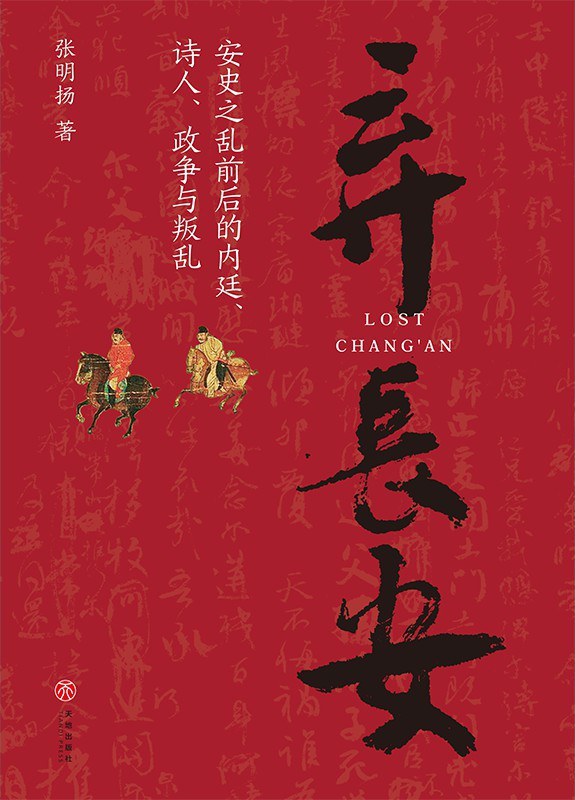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