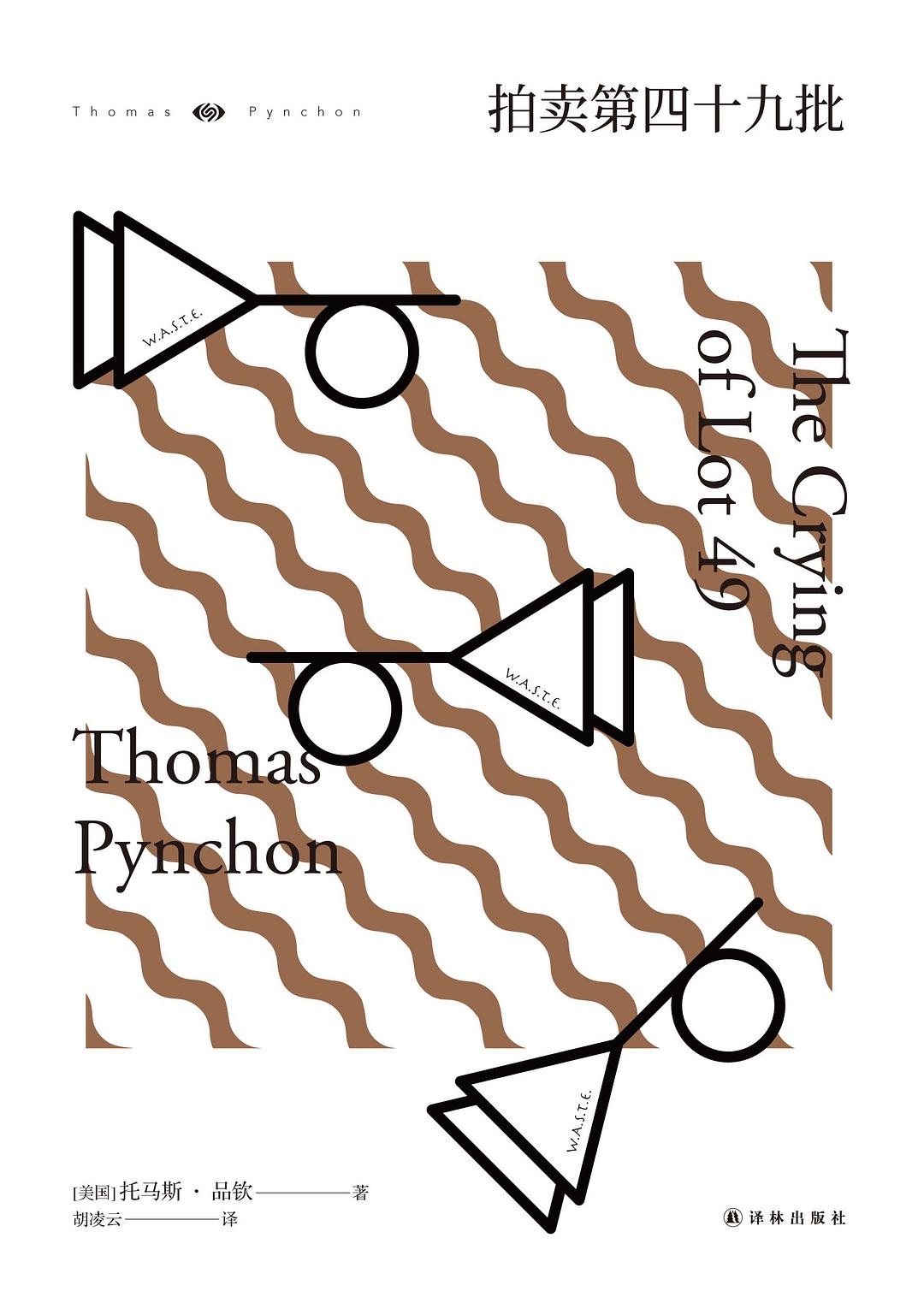
女主人公奥狄芭是一位20世纪美国典型的家庭主妇,一次聚餐回到家后,她发现自己已被她的已故情人、加利福尼亚房地产巨头皮尔斯提名为遗嘱执行人。于是奥狄芭离开洛杉矶赴皮尔斯的“大本营”——圣纳西索进行遗产调查事宜。调查过程中的许多发现,都毫无例外地指向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下邮政系统——特里斯特罗。在对这个组织的一系列调查中,她好像一直在接近真相,答案却又似是而非。
纷繁杂乱的线索使奥狄芭陷入迷茫,她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存在“特里斯特罗”,她或许只是皮尔斯设置的骗局受害者,又或者一切都是她自己的疯狂幻觉。作为“第四十九批拍卖品”进行拍卖的一组邮票,似乎成为解开特里斯特罗之谜的关键。
小说通过迷宫式的叙事和对熵增理论、测不准原理的借用,描绘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全景,道出了在无序、空虚、没有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尴尬处境,展现了鬼才品钦诡谲的视角及其对杂糅、戏仿等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
编辑推荐
▲ 品钦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易读懂,又能全面反映其独特创作风格的一部。
▲ 入选美国《时代》周刊百部英语小说佳作。
▲ 集探寻秘密、烧脑侦探、后现代神秘宗教于一身。
▲ 精致而厚重,延续品钦的一贯主题——全人类的空虚和全社会的谵妄。
作者简介
托马斯•品钦,生于1937年5月8日。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著有《V.》《拍卖第四十九批》《万有引力之虹》《葡萄园》《梅森和迪克逊》《反抗时间》《性本恶》《尖锋时代》,以及短篇集《慢慢学》。1974年因《万有引力之虹》被授予美国全国图书奖。
精彩书评
《拍卖第四十九批》发生在这个亦悲亦喜的宇宙中,伴着偏执狂的闹剧和令人心碎的形而上的独白,让人一眼认出这就是品钦的王国。它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吗? 没错,只要你别忘记它所侦探的是藏于一切万有之中的那个秘密。
——《时代》周刊
荒诞、双关和讽刺的喷发。
——《纽约时报》
散文大师的手笔……品钦错综复杂的符号体系一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芝加哥论坛报》
品钦的口语化文字非常随性,带着厚重的美国风韵,以至于你会忘记它是刻意编造出来的。
——《新闻周刊》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一个夏日午后,俄狄帕·玛斯夫人从一个特百惠家庭派对上回了家。女主人在奶酪火锅里也许放了太多的酸樱桃酒,以至于没发现她,俄狄帕,已被指定为一个名叫皮尔斯·印维拉蒂的人的遗产执行人,或者说按她的理解,女遗产执行人。那位加州地产巨子曾在业余时间白扔了两百万美金,但依然留下了足够丰厚的遗产,让清点工作不是一个虚职。俄狄帕站在起居室里,凝视着电视机死绿色的“眼睛”,口中念叨着上帝,只希望一醉方休。但她办不到。她想起马兹特兰的一间旅馆客房,门刚被撞开,似乎这样直到永久,惊起了大堂里的两百只鸟儿;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外斜坡上的日出,坐在坡上的人们都没见过,因为坡面朝西;巴托克管弦乐队协奏曲第四乐章中一个索然忧郁的调子;一个涂白了的杰·古尔德雕像放在床头一个相对太窄的书架上,她总是止不住担忧它总有一天会砸到他们。她想,那或许便是他的死因,在梦中,被宅子里唯一的偶像砸中?这想法只能让她发出无助的大笑。你真混账,俄狄帕,她对自己或是对房间说,而房间早就明白这一点。
那封信是洛杉矶的瓦普·韦斯福·库比切克和麦克明戈斯律师事务所发出的,签名的是一个叫梅兹格的人。信中说皮尔斯在春天去世了,但他们最近才发现遗嘱。梅兹格会担任遗嘱联合执行人,并在任何可能引发的法律诉讼中担任特别顾问。在日期为一年前的附加条款中,俄狄帕也被指定来执行遗嘱。她试图回忆当时有什么不寻常的事件发生。在这个下午的剩余时光中,她到松林中的金纳莱特中心的市场去买意大利乳清奶酪,听听商店里的背景音乐(今天,她来到挂着珠帘的入口时,听到的是韦恩堡18世纪乐团录制的集注版维瓦尔第小笛协奏曲第四小节,博伊德·比瓦领衔独奏);然后从香草园取来她晒干的墨角兰和甜罗勒,阅读最新一期《科学美国人》中的书评,然后堆叠千层面,给面包抹蒜蓉,撕扯罗曼莴苣叶,最后,启动烤箱,开始调制酸柠威士忌迎接回家的丈夫,文德尔· “马丘”·玛斯,她想了又想,回忆起一大堆看起来多少有些雷同的日子(她难道不是第一个承认这个现象的人吗?),它们就像一副魔术师的扑克,都微妙地指向同一处,受过训练的眼睛立刻就能辨出与众不同的那一张。直到《亨特利和布瑞金利》这节目播了一半,她才想起来去年某天凌晨三点左右接到的一个长途电话,来自一个她完全不知道的地方(到现在他留下了一本日记),声音带着很重的斯拉夫口音,自称是特兰西瓦尼亚领事馆二秘,正在寻找一只逃跑的吸血蝙蝠;声音变调成了滑稽的美国黑人腔,然后是充满敌意的墨西哥裔黑帮土话,满嘴“我操”和“基佬”;接着是一个盖世太保军官盘问颤抖的她在德国有没有亲属,最后是他的拉蒙特·克兰斯顿 的腔调,那个他当初去马兹特兰一路上使用的声音。“求你了,皮尔斯,”她终于能插上一句话,“我想我们早已经 — ”
“但是玛戈,”电话那头依然兴致盎然,“我刚从韦斯顿警察总长那儿来,那个老花花公子是被杀死奎肯布什教授的同一杆吹管枪干掉的。”诸如此类的鬼话。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她说。马丘已经翻过身来注视着她。
“你干吗不挂了?”马丘提出了理智的建议。
“我听见啦。”皮尔斯说。“我想现在是影子对文德尔·玛斯来一次小小拜访的时候了。”接着,一片彻底的死寂降临。那就是她最后一次听见的他的声音。拉蒙特·克兰斯顿。那个电话可能来自任何方向,任何远处。在通话后的几个月里,这个无言的不确定性转换为那些被唤起的记忆:他的面容、身体、他给她的东西,以及那些她不时试图忘记的他的言辞。它占据了他的位置,并把他带到了被遗忘的边缘。影子等了一年才拜访。但到来的是梅兹格的信。皮尔斯去年打电话是为了告诉她关于这个附加条款吗?还是说他是后来才决定的,因为她被激怒的态度和马丘的冷淡?她感到被暴露了,被耍弄了,被压制了。她这辈子还没执行过任何遗嘱,不知如何下手,不知该如何告诉洛杉矶的律师事务所自己不知如何下手。
“马丘,宝贝。”她无助地叹道。
马丘·玛斯正好到家,推开纱门。“今天又失败了。”他打开了话匣子。
“听我说。”她也开始了。但还是让马丘先吐为快。
他是个在半岛那一头工作的DJ,经常因为职业遭受良心危机的折磨。“那些东西我一点都不相信,俄狄 。”这是他的惯常表述。“我试了,但真的无能为力。”他陷得很深,不是她
所能触及的,所以这种时刻常常令她恐慌。也许一直是因为看到她将要失控,他自己才能够恢复理智。
“你太敏感了。”是的,她想说的也很多,但这是脱口而出的一句。无论如何,这是真感触。他曾经当过几年的汽车推销员,极其了解那个职业的工作时间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极端的折磨。每天早晨马丘要刮三次上唇,三次深入毛孔除掉任何可能冒头的胡须,新刀片都带着血,但他并不停手;购置的都是无垫肩的西服,然后送到裁缝那儿把翻领改得不同寻常地狭窄,头发只用水洒洒,像杰克·莱蒙一样使劲往后梳,去进一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每次看见锯末,甚至铅笔屑,他都会打个哆嗦,因为他的同行用这类东西来封堵有问题的汽车传动。虽然他节制饮食,但每当看见俄狄帕往他的咖啡里加蜜还是无法忍受,因为蜜和一切黏性液体都让他焦虑,让他清晰地想起那些混进机油、偷偷填进活塞和汽缸壁之间的玩意儿。他有一天晚上愤而离开一个聚会,因为有人使用了“奶油泡芙”一词,在他听来带有恶意。派对的主人是位一直在谈论糕点制作技术的匈牙利难民糕点师傅,但你的马丘是个“薄皮” 。
但至少他对汽车是有信心的。可能过度了,但怎么能不过度呢?当他看见比他穷的黑人、老墨和白佬一周七日源源而至,开着烂到极致的车来以旧换新:这些车就像是这些人,他们的家庭和他们全部生活的装了发动机的金属扩展版,赤裸裸地等待任何人,像他这样的陌生人,来观察歪扭的车架,生锈的底盘,保险杠重新漆过,虽然颜色只有细微差别,即便没让马丘郁闷,也已经足以导致贬值, 车里弥漫着孩子的、超市廉价酒的、两代或者三代吸烟者的或者仅仅是尘土的气息 — 当这些车辆得到清理时,你不得不面对这些生命的残余物,而且没法确认哪些东西是真的不想要了(他认为属于这一类的极少,因为他担心人们会把大多数东西拿走保存),哪些东西是被(也许悲剧性地)遗忘在车里:剪下来的承诺能省个五分一毛的优惠券、赠品券、宣传超市特价的粉红色小传单,烟蒂,缺齿梳子,求助广告,电话本上撕下来的黄页,来自旧内裤或是已成为古董的裙子的碎布头,它是用来擦掉挡风玻璃上呼吸导致的水汽,以便让你看见你所能看见的,一部电影,你渴望的一个女人或一辆汽车,一个可能为了练练手而截住你的警察,一切大大小小的玩意儿都有着一致的外观,就像一盘绝望制成的沙拉,浇上灰烬、凝结的废气、尘土和人体排泄物的灰色酱汁 — 这让他一看就恶心,但他不得不看。如果那完全就是家废车处理厂,他还可能挑挑拣拣,算是个工作:导致每次车祸的暴力对他来说少见而遥远得不可思议,因为每一个死亡,除非它降临到我们头上,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以旧换新的无尽祭祀仪式,周复一周,从来没达到暴力或鲜血那个境界,所以对容易受影响的马丘来说实在是因为太过合理而难以接受。即便长期面对无差别的灰色恶心物已经让他具有免疫力,他依然无法接受每个车主、每个影子排队前来,只是为了把那个有划痕的、有故障的自己的版本换成另一个,但依旧是另一个人生活的毫无未来的在汽车上的投射。看起来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对于马丘来说太恐怖了,是无尽而繁复的乱伦。
俄狄帕不理解他为什么到此时依旧会被烦扰。他娶她时已经在KCUF电台工作了两年,早已远离了那块位于惨淡轰鸣的大动脉上的车行,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对于年纪大些的丈夫们一样。也许,天保佑,他该去参战,林中的日本鬼子,虎式坦克里的德国佬和夜里吹号的黄种人对他来说也许能比他惶惶不安地待了五年的地方更快被遗忘。五年。当他们满身大汗地醒来或是用噩梦中的语言惊叫时,对,你抱住他们,他们能够镇定下来,有一天他们能够遗忘:她了解这一点。但马丘何时才能遗忘?她怀疑那个DJ职位(这个工作是通过他担任KCUF广告经理的好友拿到的,这位好友每周访问车行一次,车行是电台赞助商)只是让流行金曲二百首,甚至是那些从机器里吱吱打出来的新闻记录 — 那些满足青少年趣味的虚假梦境 — 来充当他和车行之间的缓冲区。
他对车行有着太多的信任,而对电台毫无信任。但此刻看着他,在起居室暗淡的灯光中像一只大鸟滑翔着向结着冷凝水的满满一调酒器的烈酒飞去,从他涡环的中央发出微笑,你会觉得一切都非常平和、纯净、安详。
直到他张嘴说话。“今天芬奇,”他边倒酒边说,“把我叫去,想谈谈我的形象,他不喜欢的形象。”芬奇是节目总监,马丘的宿敌。“我现在太色眯眯了。我应该成为的是一个年轻的父亲,一位兄长。这些小妞打电话进来提出各种要求和赤裸裸的欲望,在芬奇听来,这些也在我说的每个字里悸动。所以,如今我必须把所有电话交谈录下来,芬奇会把他认为有害的东西删掉,这意味着我这头无话可说了。检查制度,我告诉他,‘告密者’,我嚷嚷着,然后逃跑了。”这样的对抗,他和芬奇每周可能都会有一次。
她把梅兹格的来信递给他看。马丘知道她和皮尔斯之间的一切:在马丘和她结婚一年前,关系就结束了。他读了信,随着一连串逃避的眨眼躲开了。
“我现在怎么办?”她说。
“哦,别问我啊,”马丘说,“你找错人了。我不行。我连咱们的收入所得税表都不会填。执行遗嘱这件事,我可没法指导你。去找罗斯曼。”那是他们的律师。
“马丘。文德尔。我们早完了,在他往遗嘱上写我的名字之前。”
“嗯,嗯,我没别的意思,俄狄。我只是帮不上忙。”
于是她第二天一早便照办了,去找罗斯曼。在化妆镜前花了半个小时,沿着眼皮画了又画,总是在抬手之前画糟了或是抖得厉害。她几乎彻夜未眠,因为凌晨三点时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铃声能把人吓出心脏病,它破空响起,怠倦和尖厉交替着。他俩立刻就醒了,瘫在床上,最初几声铃响时几乎不想看对方。最终,她感觉自己接了也无妨,便拿起了话筒。是希拉瑞斯医生,她的缩头师,或称心理治疗师。但他听起来和皮尔斯假装盖世太保军官差不多。
“我没吵醒你,对吧。”他毫无感情色彩地说。“你听起来吓坏了。药吃得如何?不管用?”
“我不会吃那些药。”她说。
“你感觉受到了它们的威胁?”
“我不知道它们的成分。”
“你不相信它们只是镇静剂。”
“我信任你吗?”她并不信任,而他接下来所说的解释了其中缘由。
“我们还需要一百零四步才能走到桥上。”他干笑着。这桥被称为代布鲁克,是他给实验起的小名,他帮助社区医院测试LSD — 25、麦斯卡灵、裸盖菇素和相关药物在大样本的城郊主妇身上的效应。通向内心的桥。“你何时能让我们把你加到我们的日程里?”
“不,”她说,“你还有五十万人可供挑选。现在是凌晨三点。”
“我们需要你。”她床前横空出现了在我们所有邮局前张贴的山姆大叔的著名肖像,他的双眼闪着不健康的光芒,他下陷的双颧抹了太多的胭脂,他的手指直指她的眉心。我需要你。她从不敢问希拉瑞斯医生原因,怕他的一切回答。
“我如今正在幻觉之中,我不需要药物来创造它。”
“别向我描述它,”他迅速接上,“好吧。你还有其他什么想说的吗?”
“难道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吗?”
“我想是这样的,”他说,“我有过这种感觉,不是心灵感应,但有时候和病人亲善是件奇妙的事。”
“但这次不是。”她挂断了电话。接下来她无法入睡。不过假如吃了他给她的药,那就废了。真的废了。她并不想以任何方式上瘾。她以前告诉过他这一点。“那么,”他耸耸肩说,
“你对我也不上瘾? 那就离开吧。你被治愈了。”
她并未离开。并不是这个缩头师对她施展了某种黑暗的力量,只是留下来更容易些。谁知道她哪天会被治愈? 他不知道,这一点他自己都承认了。“药片是不一样的。”她争辩道。
希拉瑞斯只是对她做了个鬼脸,一个他以前做过的鬼脸。他最喜欢使用这些偏离正统的开心小动作。他的理论是一张面孔和一个墨迹测验的墨迹一样是对称的,像一个主题统觉测验的图片一样讲述了一个故事,像一个建议词一样激发了一种反应,那么为什么不来一张呢?他宣称曾经用他的37号鬼脸“傅满洲”(很多鬼脸像德国交响曲一样有一个号码和别称)治好了一个癔病者。这鬼脸是用两根食指将眼角向上推得眼睛眯缝起来,用两根中指把鼻孔扯开,把嘴巴扯宽,露出舌头,希拉瑞斯扮起来真是非常吓人。事实上,当俄狄帕的山姆大叔幻觉消退之后,取而代之的正是这个傅满洲的面孔,在黎明来临前的几个小时中一直陪伴着她。它让她完全无力收拾心绪去见罗斯曼。
但罗斯曼也度过了一个不眠夜,在前夜郁闷地看完了佩瑞·马森的电视节目,那是妻子喜欢的,但罗斯曼自己对它的感觉却是激烈矛盾的,既非常想当一位像佩瑞·马森那样成功的辩护律师,但因为这并不可能,所以又同时想通过贬低佩瑞·马森来摧毁他。俄狄帕进门时看到她所信任的家庭律师正在带着急急的负罪感把一沓尺寸、色彩各异的纸塞进一个写字台抽屉时,不免感到几分惊讶。她知道那是《起诉佩瑞·马森,一份并不那么虚构的起诉书》的初稿,他自从电视节目开播以来一直都在写作之中。
“在我印象里,你看起来从来没有这么感到负罪过。”俄狄帕说道。他们经常去同一个群体理疗班,结伴开车去的还包括一位来自帕罗阿图、认为自己是个排球的摄影师。“这是个好兆头,不是吗?”
“你没准是佩瑞·马森派来的侦探。”罗斯曼说。思考片刻后他又接上了一串“哈,哈”。
“哈,哈。”俄狄帕回应道。他们望着彼此。“我得执行一份遗嘱。”她说。
“哦,那就执行吧。”罗斯曼说。“别为我耽搁。”
“不。”俄狄帕说着,道出了一切。
“他为何这么做?”罗斯曼读了信之后很迷惑。
“你是说死掉?”
“不是,”罗斯曼说,“是点名让你来帮助执行。”
“他这个人没法预料。”二人共进午餐。罗斯曼试图在桌子底下用脚挑逗她。她穿着高筒靴,感觉不到什么。所以,既然屏蔽良好,她决定不大惊小怪。
“和我私奔吧。”咖啡端上来时,罗斯曼说。
“去哪儿?”她问。他立刻就哑巴了。
回到办公室之后,他简单列出了她需要办理的事项:仔细研究账目和产业、通过遗嘱认证、收取所有债务、清点资产、拿到房地产评估、决定清算和保留、清偿债务、了解税务、分配遗产……
“嘿,”俄狄帕说,“我就不能找个人来帮我打理吗?”
“我,”罗斯曼说,“我干其中一部分,没问题。但你连兴趣都没有?”
“对什么的兴趣?”
“对你可能会发现的秘密的兴趣。”
随着事态的发展,她会拥有各种各样的启示。并不是关于皮尔斯·印维拉蒂或者她自己的,而是关于一些遗留的、但此前没有介入的事物。有那么一种缓冲和隔离的感觉,让她感到强度的缺乏,就像是看一场电影,稍微感到有那么一点失焦,而放映员拒绝修正,而且温和地把她诱入了一个好奇的、长发公主式的郁沉姑娘的角色。魔术般地,她被困在金纳莱特的松林和咸雾中。寻找着人能说出,喂,放下你的头发。当发现是皮尔斯时,她快乐地拔出发针并取下发卷,头发沙沙响着如一次纤巧的雪崩般滑落,只是当皮尔斯才爬了一半时,她可爱的头发被某种邪恶的魔法变成了一副巨大的没挂住的假发,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但他依然胆大包天,也许是从他那一大沓信用卡中抽出一张捅开了她塔楼的门,走上了海螺般的阶梯,如果他真正诡计多端的话起先就爬上来了。但他们之间的一切从未逃脱过那座塔的限制。在墨西哥城,他们不经意间逛进了美丽的西班牙流放者雷美迪奥斯·瓦罗的画展:在名为“博丹多·艾尔·曼托·特雷斯特里”的三联画的中央一幅中,是很多位有着心型面孔、巨大眼睛和金丝秀发的纤弱姑娘,被关在一座圆塔顶部的屋子里,绣制着一条滑出狭缝窗的挂毯,进入虚空,毫无希望地想要填满虚空:因为大地上所有的其他建筑、生灵,所有的浪涛、船只和森林都包含在这幅挂毯中,挂毯就是世界。俄狄帕,很任性,站在画作前就哭。没有人留意到:她戴着暗绿色的泡泡形太阳镜。她曾经有一阵觉得罩在眼眶周围的镜框足够水密,能够让流出的眼泪注满镜片后面的空间而绝不干涸。她能以那样的方式永远带着她那一刻的伤悲,透过那些眼泪来观察一个被折射的世界,透过那些特别的眼泪,就好像哭泣和哭泣之间有着未知但却重要的不同指数。她曾经低头俯视双足,因为这么一幅画作她明白了她所站立之处是在几千里外她自己的高塔中刚刚编织出来的,并且碰巧了解到它叫墨西哥,所以说皮尔斯并未带她逃离任何事物,私奔并未发生。她究竟希望逃离什么?这样一位被困的女士,有着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很快便意识到她的高塔,它的高度和建筑式样,碰巧与她的自我意识相似,而把她保留在那儿的其实是魔力,它匿名而恶意,从外界观察她,不带任何缘由。因为除了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女性特有的狡猾之外并没有其他机能去考察这种无形的魔力,去了解它的机理,测量它的场强,计算它的力线,她也许会回归迷信,或是捡起一种有用的爱好诸如刺绣,或者变疯,或者嫁给一个DJ。如果高塔到处都是,而前来解救的骑士没有能够战胜其魔力的证据,那还能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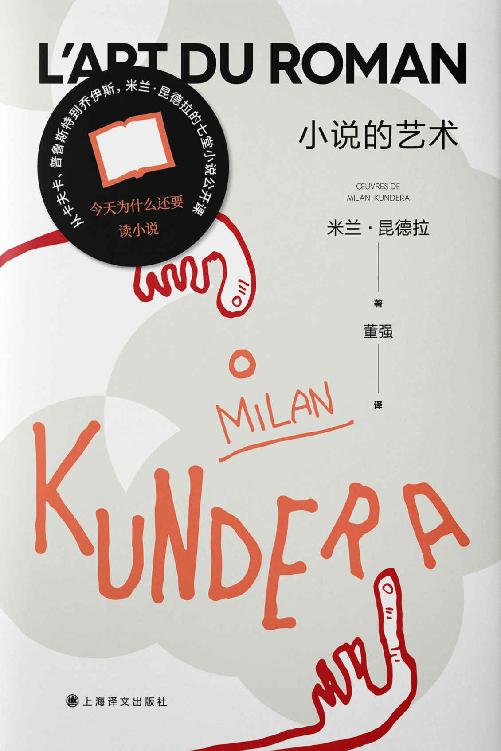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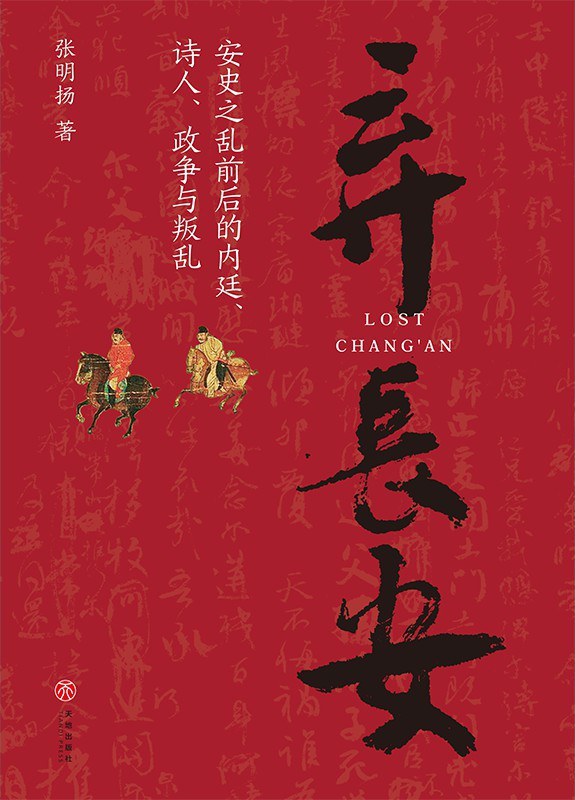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