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台》人刁顺子踏实肯干,带着几个兄弟承接各种演出装台的活。顺子有过三次婚姻,老婆抛弃了他留下女儿刁菊花,第二个老婆得癌症去世了,带过来一个女儿韩梅,第三房老婆蔡素芬漂亮温顺,却遭到自己容貌不佳沦为大龄剩女的女儿菊花的百般刁难,心理扭曲的菊花把蔡素芬和大学放假回来的韩梅视为眼中钉,家里频频爆发“女人大战”顺子在外面点头哈腰招揽生意、没日没夜的卖苦力赚钱,回家又得面对被女儿折腾的破乱不堪的家。韩梅、蔡素芬忍受不了菊花纷纷离开了这个家……小说刻画人物手法细腻,故事跌宕起伏,命运看似之无常又有常,以一个装台人为视角,描写西京城里人生百态。
编辑推荐
荣获“201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冠军。
颁奖词这样描述《装台》:戏是被照亮被注视的人生,装台人则站在人生的侧面。作家从人们习焉不察的世界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小说写古往今来无从逃遁的生命之重,曲尽悲欢,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人生经验的复杂纹理,细密而结实。
《装台》中有世情的苦涩,众生在人世间的奋斗、挣扎,无奈和无力。但作者似乎无意于在简单的层面上批评时代的局限和社会分工与分配的“不合理”,或者替无从自我表达的所谓的“底层”代言,而是书写古往今来横亘宇内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人之生命中所必须承受之重。陈彦从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世界中发现并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种形象表达了他对带有根本性的人之生存境况的感受与思考。
颁奖词这样描述《装台》:戏是被照亮被注视的人生,装台人则站在人生的侧面。作家从人们习焉不察的世界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小说写古往今来无从逃遁的生命之重,曲尽悲欢,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人生经验的复杂纹理,细密而结实。
《装台》中有世情的苦涩,众生在人世间的奋斗、挣扎,无奈和无力。但作者似乎无意于在简单的层面上批评时代的局限和社会分工与分配的“不合理”,或者替无从自我表达的所谓的“底层”代言,而是书写古往今来横亘宇内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人之生命中所必须承受之重。陈彦从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世界中发现并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种形象表达了他对带有根本性的人之生存境况的感受与思考。
前言序言
因无法忘却的那些记忆
——长篇小说《装台》后记
陈彦
我在文艺团体生活过好几十年,当离开的时候,忍不住独自怆然泪下。我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觉得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声,皮开肉绽地撕裂开了。
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一种人们称之为艺术家的人群。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做同事,做伙伴,做朋友,相互砥砺、激荡,也相互雕刻、形塑。几十年下来,许多形象,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地存活下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些形象、这些故事,是够我受用此生了。
也许我离开他们的时间,还有些短,距离还有点近,形象、故事,还都混沌如雾中庐山,写作时,一提就是一嘟噜,无法删繁,无从简约,几次尝试,都像街边的杂货铺,已经摆得层层叠叠,压胳膊枕腿儿了,可还有许多要紧的东西,觉得没摆上去,因此,也就只好暂时放弃。
可咋放弃,有一群人,还是总在我眼前晃悠,他们是这个群体以外的人,但又是这个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装台人。
所谓装台,对于这个行业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释的。自然舞台,永远就是那样空空旷旷的,可以行车走马,一旦演出,要在这个舞台上布置出一个故事的典型环境来,就需要装台。装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布景,二是灯光。布景还分软景、硬景,软景就是那些用平布画的景,上面可能有楼房、山脉、村庄、宫殿,但却是可以折叠的,一叠起来,一包袱就可以提溜走。而硬景包括那些可以行走、运动、升降的平台、山峦、巨石等,一件是一件,有时一组平台就能装几卡车,装在舞台上,也是要能力挺万钧的。现在舞台演出特别讲“创新”,讲“震撼”,内容创新不了,心灵震撼不动,就得上感官,有些演出,一组平台是要站上去百十号人,甚至数百号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不钢筋结构,不涡轮增压,岂能在掌声中精彩谢幕?灯光就更神奇了,什么花样都能变幻出来,照明已经是它的副产品,重要的,据说是为舞台铸灵魂。要为舞台铸造灵魂谈何容易,那层层叠叠、起起落落的神秘光斑、魔幻魅影,就需要大量的光源去支撑。而这光源,就来自数百只,甚至上千只作用不同的灯光的化合勾兑,□终才能形成不知天上人间今夕何年的效果。而一只灯,有的重达百斤以上,这么大的劳动量,自然就在传统的七十二行以外,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来:装台。
过去的老戏楼,几乎不用装,有钱人家的戏台,本身就是雕梁画栋的,请一班戏来,所谓布景、道具,也就一桌、二椅、三搭帘,“搭”是桌椅的搭布,“帘”是门帘、床帏,为了表演,做些必要的遮挡而已。那时没有装台这一说。演一晚上戏,就一个“捡场的”,桌椅搬上搬下,床帏挪进挪出,有时还兼管着后台的服装、衣帽,业内叫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后来开始演时装戏了,就讲究一点环境的真实,过去靠表演就能说清楚的进门、跳墙、织布、纺线之类的做工戏,都用实物代替了,进的是真门,翻的是真墙,织布、纺线车也都是真木实料的能推能转,以至弄得越来越邪乎,有的演出,竟然把真驴真马、真汽车、真飞机都拽上了舞台,装台这一行,不火都不由人了。
其实□早装台,主要还是靠演出团体的自家人,乐队、演员、后勤人员一合手,毕竟是搞艺术,不是搞建筑,不是搞各种水利、土木、机械、钢铁工程,局外人焉能染指。但后来舞台装置越来越像搞建筑、水利、矿山、木材、钢铁、机械加工,这些艺术家就不得不退位了,加上那活儿,已不需太多的艺术思维,只要照技术图纸这只“猫”,画出“老虎”就是,且基本都是重体力活,因而,就把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们是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走,当然,也有始终如一,把自己无形中“钉”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爱琢磨他们的生活。他们大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洪常青”,当然,也有的,就成了他们的“吸血鬼”、“南霸天”。别看装台是个小行当,可在一个文化的热闹期,这行当就被放大了,有时几乎到处都升起了吊着巨幅广告标语的气球,那气球包裹的中心,就搭建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因此,装台又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演员,也不都是靠演唱讨生活的职业演员,有的可能是企业家,有的可能是银行家,有的可能是政治家,有的还可能是出家人,连知识分子也多有魂不守舍的,由“素心”变“荤心”,由“斗室”进“道场”,反正都在表演,都需要一个十分抢眼的舞台。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小说说到底是讲生活,他们在生活,在用给别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当然,为人装台,其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表演,也是一种人生舞台,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
我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当我准备写他们的时候,还有意与其中几位比较熟悉的,进行了长谈,并且做了好多笔记。鲁迅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小说中这些人物与故事,也在偷着向鲁迅学,是黏合起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终抟成了刁顺子这样一群特殊的装台人。
底层与贫困,往往相链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再加上贫病与其他一些生命行进装备的胡乱组装,有时连亲人也不再相亲,儿女都羞于伦常了,更遑论其他。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继而让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体面的大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抑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勾颈拥眠的动人狐仙。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法的生命意义,我们还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实的眼光去发现,去认同。
无论写作时,还是写完后,我还都没有琢磨出更多的意义,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没有整块时间去梳理这些记忆,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
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问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时间,再回刷一次屏。其实一个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饭、误了约会,都不缺交给心灵的时间。我觉得写作,就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记得几年前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的时候,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就开始给自己汇报思想,直汇报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一晚上不汇报,哪怕九、十点就上床,早上开会反倒打哈欠。前一阵看新闻,好像开会丢盹,在某个国家还是要拿大炮毙脑袋的事体。可见清醒有多重要啊。一个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盘存一下,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高兴也罢,不快也罢,能定期定时盘整回望,当更有助于明天后天那些惊人相似且带着轮回样态的生活面对。对于我,这个盘整就是写作。
业余时间,我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拧了反锁,拉了深色窗帘,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悲惨世界》,或《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霍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出了门,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四个以上的多维影像。熟人见了,还疑似我目中无人了。读书与写作,对我是一种盘存,更是一种能孤独享用的快乐与休息,无论生活中,你经历了多少无奈、伤害与精神痛楚,一旦进入写作,那些神经都会变得麻木起来,只有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
感谢作家出版社不弃,副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亲自审读拙作,并给予鼓励,责任编辑李亚梓老师,更是认真负责,为成书,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长途资讯费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著名作家刘震云、阿来先生拨冗推介,让《装台》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在此一并谢忱!
2015年5月26日于西安
——长篇小说《装台》后记
陈彦
我在文艺团体生活过好几十年,当离开的时候,忍不住独自怆然泪下。我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觉得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声,皮开肉绽地撕裂开了。
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一种人们称之为艺术家的人群。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做同事,做伙伴,做朋友,相互砥砺、激荡,也相互雕刻、形塑。几十年下来,许多形象,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地存活下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些形象、这些故事,是够我受用此生了。
也许我离开他们的时间,还有些短,距离还有点近,形象、故事,还都混沌如雾中庐山,写作时,一提就是一嘟噜,无法删繁,无从简约,几次尝试,都像街边的杂货铺,已经摆得层层叠叠,压胳膊枕腿儿了,可还有许多要紧的东西,觉得没摆上去,因此,也就只好暂时放弃。
可咋放弃,有一群人,还是总在我眼前晃悠,他们是这个群体以外的人,但又是这个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装台人。
所谓装台,对于这个行业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释的。自然舞台,永远就是那样空空旷旷的,可以行车走马,一旦演出,要在这个舞台上布置出一个故事的典型环境来,就需要装台。装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布景,二是灯光。布景还分软景、硬景,软景就是那些用平布画的景,上面可能有楼房、山脉、村庄、宫殿,但却是可以折叠的,一叠起来,一包袱就可以提溜走。而硬景包括那些可以行走、运动、升降的平台、山峦、巨石等,一件是一件,有时一组平台就能装几卡车,装在舞台上,也是要能力挺万钧的。现在舞台演出特别讲“创新”,讲“震撼”,内容创新不了,心灵震撼不动,就得上感官,有些演出,一组平台是要站上去百十号人,甚至数百号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不钢筋结构,不涡轮增压,岂能在掌声中精彩谢幕?灯光就更神奇了,什么花样都能变幻出来,照明已经是它的副产品,重要的,据说是为舞台铸灵魂。要为舞台铸造灵魂谈何容易,那层层叠叠、起起落落的神秘光斑、魔幻魅影,就需要大量的光源去支撑。而这光源,就来自数百只,甚至上千只作用不同的灯光的化合勾兑,□终才能形成不知天上人间今夕何年的效果。而一只灯,有的重达百斤以上,这么大的劳动量,自然就在传统的七十二行以外,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来:装台。
过去的老戏楼,几乎不用装,有钱人家的戏台,本身就是雕梁画栋的,请一班戏来,所谓布景、道具,也就一桌、二椅、三搭帘,“搭”是桌椅的搭布,“帘”是门帘、床帏,为了表演,做些必要的遮挡而已。那时没有装台这一说。演一晚上戏,就一个“捡场的”,桌椅搬上搬下,床帏挪进挪出,有时还兼管着后台的服装、衣帽,业内叫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后来开始演时装戏了,就讲究一点环境的真实,过去靠表演就能说清楚的进门、跳墙、织布、纺线之类的做工戏,都用实物代替了,进的是真门,翻的是真墙,织布、纺线车也都是真木实料的能推能转,以至弄得越来越邪乎,有的演出,竟然把真驴真马、真汽车、真飞机都拽上了舞台,装台这一行,不火都不由人了。
其实□早装台,主要还是靠演出团体的自家人,乐队、演员、后勤人员一合手,毕竟是搞艺术,不是搞建筑,不是搞各种水利、土木、机械、钢铁工程,局外人焉能染指。但后来舞台装置越来越像搞建筑、水利、矿山、木材、钢铁、机械加工,这些艺术家就不得不退位了,加上那活儿,已不需太多的艺术思维,只要照技术图纸这只“猫”,画出“老虎”就是,且基本都是重体力活,因而,就把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们是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走,当然,也有始终如一,把自己无形中“钉”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爱琢磨他们的生活。他们大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洪常青”,当然,也有的,就成了他们的“吸血鬼”、“南霸天”。别看装台是个小行当,可在一个文化的热闹期,这行当就被放大了,有时几乎到处都升起了吊着巨幅广告标语的气球,那气球包裹的中心,就搭建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因此,装台又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演员,也不都是靠演唱讨生活的职业演员,有的可能是企业家,有的可能是银行家,有的可能是政治家,有的还可能是出家人,连知识分子也多有魂不守舍的,由“素心”变“荤心”,由“斗室”进“道场”,反正都在表演,都需要一个十分抢眼的舞台。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小说说到底是讲生活,他们在生活,在用给别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当然,为人装台,其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表演,也是一种人生舞台,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
我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当我准备写他们的时候,还有意与其中几位比较熟悉的,进行了长谈,并且做了好多笔记。鲁迅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小说中这些人物与故事,也在偷着向鲁迅学,是黏合起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终抟成了刁顺子这样一群特殊的装台人。
底层与贫困,往往相链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再加上贫病与其他一些生命行进装备的胡乱组装,有时连亲人也不再相亲,儿女都羞于伦常了,更遑论其他。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继而让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体面的大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抑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勾颈拥眠的动人狐仙。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法的生命意义,我们还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实的眼光去发现,去认同。
无论写作时,还是写完后,我还都没有琢磨出更多的意义,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没有整块时间去梳理这些记忆,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
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问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时间,再回刷一次屏。其实一个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饭、误了约会,都不缺交给心灵的时间。我觉得写作,就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记得几年前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的时候,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就开始给自己汇报思想,直汇报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一晚上不汇报,哪怕九、十点就上床,早上开会反倒打哈欠。前一阵看新闻,好像开会丢盹,在某个国家还是要拿大炮毙脑袋的事体。可见清醒有多重要啊。一个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盘存一下,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高兴也罢,不快也罢,能定期定时盘整回望,当更有助于明天后天那些惊人相似且带着轮回样态的生活面对。对于我,这个盘整就是写作。
业余时间,我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拧了反锁,拉了深色窗帘,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悲惨世界》,或《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霍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出了门,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四个以上的多维影像。熟人见了,还疑似我目中无人了。读书与写作,对我是一种盘存,更是一种能孤独享用的快乐与休息,无论生活中,你经历了多少无奈、伤害与精神痛楚,一旦进入写作,那些神经都会变得麻木起来,只有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
感谢作家出版社不弃,副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亲自审读拙作,并给予鼓励,责任编辑李亚梓老师,更是认真负责,为成书,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长途资讯费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著名作家刘震云、阿来先生拨冗推介,让《装台》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在此一并谢忱!
2015年5月26日于西安
精彩书摘
一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
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神使鬼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
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地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发眯瞪的断腿狗,一骨碌爬起来,汪汪叫着,跑回房里,去寻找自己□□的保护伞顺子去了。
那阵儿,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迸碎的陶片,噌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她的小腿,差点没击中要害处,吓得她急忙撸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儿溜回了房里。
断腿狗正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踮在地上,还惶悚得一抽一抽的,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叨咕了一句:“惯得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就再没下话了。
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多也就嘟哝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管人了。蔡素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刁菊花有这么厉害,她才回来□□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
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偎到床边哄,手里剥了根香蕉,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
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
这话还算管用,蔡素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留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地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磨着,蔡素芬突然张大嘴,美美地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哟一声,蔡素芬就顺势把他腕拢到了床上。
虽然才是晚上九点多,顺子就灭了灯。
断腿狗看到顺子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翻动,又早早没了灯,就有些着急,对着床汪汪叫个不停,顺子骂:“没良心的东西,见不得别人锅里米汤起皮,难道也见不得我米汤锅里沁点油花花。”把蔡素芬惹笑了,扑哧扑哧的,如放了气一般的绵软无力。
正在他们享乐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活时,菊花已经下楼来了,她先是上了趟厕所,然后又在水龙头接水,故意把水开得很大,冲得满池子噼啪噼啪地响,像是老天在行风暴走。顺子和蔡素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定格在一个姿势上,静静等待着。谁知菊花就在快要上楼的一刹那间,又撂出一句狠话来,像是一支毒箭,直接穿过窗户,射在了他们的心窝里:
“尾巴一揭,只要是母的,都能领上床,哼,贱种!□□!”
顺子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猛地翻起来,就要发飙。
蔡素芬却一把搂住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说:“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
顺子觉得这回是严重伤害了自己做父亲的自尊,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是咋样把你拉扯大的,你就敢说亲生父亲这样的坏话,今天无论如何,是得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可蔡素芬咋都没让他下床。蔡素芬就那样死死把他腰搂着,直到他唉声叹气的,又慢慢把身子溜了下去。
可这晚上,顺子也再耍不起做男人的威风了。
断腿狗看床上再没啥动静,也就舔了舔那条断腿,早早安寝了。
大概是睡到半夜时分,素芬突然说浑身痒痒,问:“是不是家里有虱子?”
顺子迷迷糊糊地说:“瞎说,早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了,先前有。”
“哎哎哎,都爬到我身上了,还说没有。”
顺子就开了灯,一看,是蚂蚁,还不是一个两个,越找越多,个头都一般大小,是跟猪鬃差不多粗细的那种小黑蚁。这些家伙,单个行走,几乎不容易发现,一旦集体行动起来,就是一种牵连不断线的浩荡大军。
顺子顺着蚂蚁行走的方向一看,说:“是蚂蚁搬家。咱这村子,蚂蚁多,不稀奇,小时我们经常看见蚂蚁搬家哩。”他看蚂蚁都是从房门底下钻进来的,就打开门一看,果然,月光下,一支黑色大军,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列,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经过七弯八折,□后消失在了西墙脚的一个窄洞里。这些小家伙,多数都用两个前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而跑进卧房的这些,估计都是出来找东西,或者是开小差跑散了的。素芬问咋办,顺子说:“它搬它的家,咱睡咱的觉,估计天亮就搬完了。”顺子说着,把床上的被子拿起来抖了抖,素芬就用脚,把跌在地上的蚂蚁朝死里踩。顺子急忙制止说:“别踩!”他用扫帚把那些蚂蚁都扫进灰斗里,然后拿到蚂蚁队伍前,轻轻倒了进去。
素芬就笑了,说:“你是吃斋念佛的呀?”
“唉!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
……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
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神使鬼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
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地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发眯瞪的断腿狗,一骨碌爬起来,汪汪叫着,跑回房里,去寻找自己□□的保护伞顺子去了。
那阵儿,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迸碎的陶片,噌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她的小腿,差点没击中要害处,吓得她急忙撸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儿溜回了房里。
断腿狗正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踮在地上,还惶悚得一抽一抽的,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叨咕了一句:“惯得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就再没下话了。
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多也就嘟哝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管人了。蔡素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刁菊花有这么厉害,她才回来□□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
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偎到床边哄,手里剥了根香蕉,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
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
这话还算管用,蔡素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留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地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磨着,蔡素芬突然张大嘴,美美地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哟一声,蔡素芬就顺势把他腕拢到了床上。
虽然才是晚上九点多,顺子就灭了灯。
断腿狗看到顺子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翻动,又早早没了灯,就有些着急,对着床汪汪叫个不停,顺子骂:“没良心的东西,见不得别人锅里米汤起皮,难道也见不得我米汤锅里沁点油花花。”把蔡素芬惹笑了,扑哧扑哧的,如放了气一般的绵软无力。
正在他们享乐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活时,菊花已经下楼来了,她先是上了趟厕所,然后又在水龙头接水,故意把水开得很大,冲得满池子噼啪噼啪地响,像是老天在行风暴走。顺子和蔡素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定格在一个姿势上,静静等待着。谁知菊花就在快要上楼的一刹那间,又撂出一句狠话来,像是一支毒箭,直接穿过窗户,射在了他们的心窝里:
“尾巴一揭,只要是母的,都能领上床,哼,贱种!□□!”
顺子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猛地翻起来,就要发飙。
蔡素芬却一把搂住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说:“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
顺子觉得这回是严重伤害了自己做父亲的自尊,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是咋样把你拉扯大的,你就敢说亲生父亲这样的坏话,今天无论如何,是得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可蔡素芬咋都没让他下床。蔡素芬就那样死死把他腰搂着,直到他唉声叹气的,又慢慢把身子溜了下去。
可这晚上,顺子也再耍不起做男人的威风了。
断腿狗看床上再没啥动静,也就舔了舔那条断腿,早早安寝了。
大概是睡到半夜时分,素芬突然说浑身痒痒,问:“是不是家里有虱子?”
顺子迷迷糊糊地说:“瞎说,早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了,先前有。”
“哎哎哎,都爬到我身上了,还说没有。”
顺子就开了灯,一看,是蚂蚁,还不是一个两个,越找越多,个头都一般大小,是跟猪鬃差不多粗细的那种小黑蚁。这些家伙,单个行走,几乎不容易发现,一旦集体行动起来,就是一种牵连不断线的浩荡大军。
顺子顺着蚂蚁行走的方向一看,说:“是蚂蚁搬家。咱这村子,蚂蚁多,不稀奇,小时我们经常看见蚂蚁搬家哩。”他看蚂蚁都是从房门底下钻进来的,就打开门一看,果然,月光下,一支黑色大军,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列,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经过七弯八折,□后消失在了西墙脚的一个窄洞里。这些小家伙,多数都用两个前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而跑进卧房的这些,估计都是出来找东西,或者是开小差跑散了的。素芬问咋办,顺子说:“它搬它的家,咱睡咱的觉,估计天亮就搬完了。”顺子说着,把床上的被子拿起来抖了抖,素芬就用脚,把跌在地上的蚂蚁朝死里踩。顺子急忙制止说:“别踩!”他用扫帚把那些蚂蚁都扫进灰斗里,然后拿到蚂蚁队伍前,轻轻倒了进去。
素芬就笑了,说:“你是吃斋念佛的呀?”
“唉!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
……
作者简介
陈彦,1963年出生,陕西镇安县人,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度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三次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央视播映并获电视剧“飞天奖”。出版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以及《陈彦剧作选》等。多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国务院特贴专家,文化部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精彩书评
“小说写的是由市民、农民工组织起来的舞台、装台组合,代表人物是一个装台班子的领班,刁顺子。刁顺子与他的伙伴们虽然下苦,仍然有一种责任担当,他们卑微中有自己做人的底线,苦熬中有自己生活的期待,他们的身上有人民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诚朴忠厚,吃苦耐劳,宁可亏钱,绝不亏心的种种可贵的中国精神。”
——著名作家王蒙
——著名作家王蒙
资源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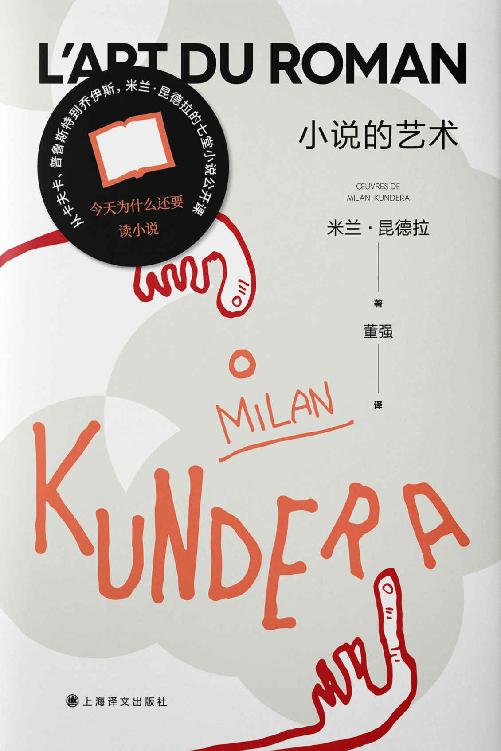
.jpg?imageMogr2/thumbnail/!1096x1600r|imageMogr2/gravity/Center/crop/1096x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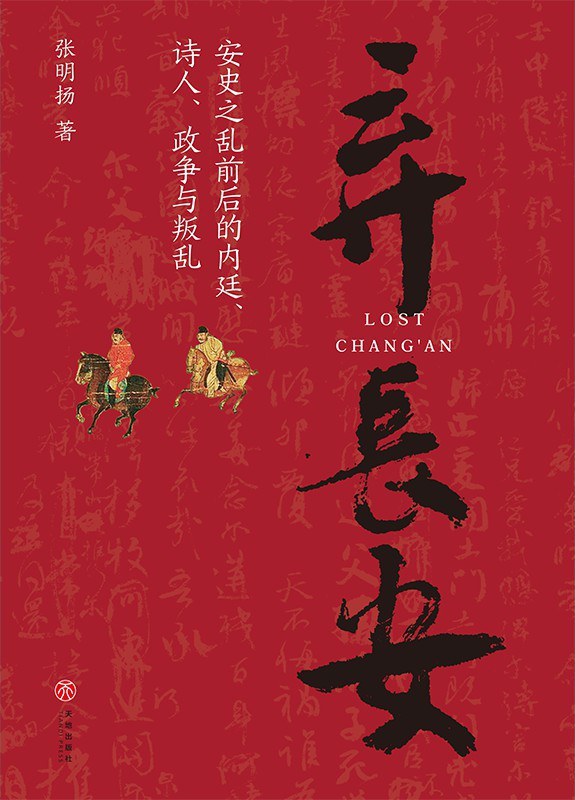

评论0